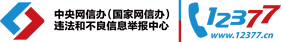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果子”不是果实,是老家对糖点心的俗称。儿时,大人哄小孩子,都要说一句:“嗯,给你买果子吃。”小孩子眼睛都亮了,忍不住“吧嗒”几下嘴,仿佛吃到甜甜的糖,惹得一阵笑声。
油果子却又不是油炸的糖点心,其实就是“油条”,奶奶叫它“油炸棍”,两根粗面片,按在一起用油炸到香脆,像棍一样,叫法形象贴切。有好事者考证,“油炸棍”起源于杭州,实为“油炸桧”之误,爱憎分明的杭州人恨秦桧害死了岳飞,把他做成面点,下油锅,炸了吃。我不喜欢这个说法,嫌秦桧这等人,炸了吃都恶心。我更喜欢叫它“油果子”,在我看来,它和童年最期盼的果子是没有区别的了。
油果子好吃。刚出锅的油果子又酥又香,吃起来一汪油。可惜能吃到新炸油果子的次数也就一两回。放冷后的油果子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不再酥脆,却有绵软的韧劲,香,可变着花样吃。可以把它卷成圆圆的一团,咬起来筋实有嚼劲;也可以放在蒸锅里热了吃,软软的,暖到心里。我最喜欢油果子泡红糖开水,又甜又软又香,是记忆中无上的美味。放时间长了,油果子水分风干,变硬,吃起来嘎嘣脆,又是别样的风味,照样好吃。前年过年,刁嘴儿子回老家,吃了几次风干油果子,喜欢得不得了,屡屡要我去买。可惜,买回来还没放干就到了他的肚里,边吃边念叨:“妈妈,怎么不是那种干干的?”儿子不知道,那种干干的油条往往是舍不得吃的大人给孩子们留下来的。
农村不如城市便利,吃一次油条不容易。邻居小鬼精滑,拿几根油条,怕别人吃,每根咬一口,宣告主权,多年被传为笑话。小时候,只有梁咀街上有卖油条的。街不大,人很多,很热闹。我看到卖油条的就走不动脚,站在那里一看就是半天。一口黑黑的锅,热烫的油翻滚,师傅切两片面,叠放在一起,用一根竹板从中间压道印,锅里一丢,油条沉下去,“滋滋”地响着,浮上来,长筷子拨一拨,翻个面,等一等,热腾腾的油条就可以出锅了。卖油条的地方常围一大圈子看客,现在想来,应该是和我一样想吃又没钱买的孔乙己们。其实,那时候,油条很便宜,我印象是2分钱一根,鸡蛋9分钱一个。上班以后,专门又到梁咀街上看了一趟,只是一条窄窄的土路,星星点点的几个小贩,早没有了炸油条的痕迹,也没有了印象里的热闹与繁华,有点失落。
生活好一点的家庭,过年时可以自家开油锅炸油条。但这是个技术活儿,村里只有陈三叔会炸。后来,我家条件有所改善,过年时也请陈三叔炸过一次油条,我怀着热切的心情看完了炸油条的全过程。复杂的程序一点不记得,只记得陈三叔在我们崇拜的目光中一脸严肃地加水、加料、揉面、抖面,那手法、板式像在制作一件艺术品。现在,食谱大全上有制作油条的方法、程序,我从不尝试,固执地认为,没有技术,全凭那几行字儿,怎么可能炸出又香又酥的油条?
走亲戚有时也能吃到油条。记忆里,母亲会“拣油果子”去走亲戚。挑一个挑子,一边是油条,一边是面条,母亲带着我去走亲戚。到了亲戚家,糖水油条吃一碗又一碗,真爽。印象里“拣油果子”去走亲戚也只有屈指可数的次数。母亲说,只有娘家人才会“拣油果子”。那时太小,不明白,现在想来,应该是那时候缺衣少食,产妇新添孩子,娘家人怕产妇吃不好,落下病,所以不怕费事,炸油条送去,让产妇吃好。这油果子里,全是至亲人的感情。
中学到了镇上,炸油条的就多了,开始习惯说“油条”,也接受了它一毛钱一根的价格,确实比乡下梁咀街上的油条更大更酥,只有香还是一样。初二时,五月的瞌睡睡不醒,地理课上,一大半人趴在桌子上睡觉。我也在朦胧间听到张黎明老师提问:“什么是‘油果子’?”点名,大家癔里巴症站起来一片,均是一脸茫然。老师给出的正确答案是:“就是油条。”问题没答上来,瞌睡倒是被全赶走了。我不能相信,土里土气的“油果子”,竟然也能走上高大上的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