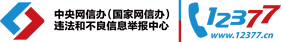前天无意中拍了张图片发在空间里,一老农肩上扛着捆柴,赶着牛羊回家。牛羊们悠闲地往回走,大概还没吃饱,边走边啃着路边的青草。领头的老黄牛见我举着相机,便仰起头,露出好奇的眼神。有位网友是集镇上的大姑娘,竟然向我提了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问我照片上羊儿旁边站的是什么。这在我看来好可笑啊,敢情她竟没见过老黄牛。说怪也不怪,现在的孩子都很金贵,三岁就进了校门,然后再从学校到单位,很少领略过农村这“广阔的天地”。我估摸着,这位姑娘应该是见过牛的,不过可能是水牛,跟照片上的黄牛有区别。
我生在深山长在深山,从小就跟着爷爷放牛,当然对牛印象深刻。大集体时代,生产队喂着很多牛,有不少跟爷爷一样的专职饲养员。记得哪本书上有这么一句话:“牛,这是农民的宝贝。”的确,当时深山里的耕作方法跟现在不一样,还没推广“麦苞间作”,种的是“一块板”,冬天靠牛翻地,春天用牛播种。后来山里人种地的方式变了,一行小麦一行苞谷,行子都靠人挖,再加上土地承包到户了,喂牛的人便越来越少。如今我们一个村子仅有两户养牛的,大大小小加起来才七头牛,硕果仅存。
骟过的公牛俗称大犍子,有黄犍子有黑犍子,是犁田的主角,拉三根绳,也是当时农村最值钱的东西。说谁谁打牌输了钱,最严重的莫过于“输了一头大犍子”。劝人戒烟,也有句话:“三年不吸烟,买头大黄犍”。说谁身体壮力气大,就说像个“黄犍子”。说话办事格外一个样,那叫“黄牛黑卵子”。好色成性的男人,往往会被比喻为“骚犍子”——当然是刚长大还没骟过的,一般含有贬义。
黄牛这东西,身大力不亏,干活靠的就是力气,拉犁耕地是他的天职。教会没入门的牛耕地叫“调牛”,那可不是个好差事,既要有力气,还要懂技术。最好面相要“恶”,声音要响亮,要有一定的气势,不然牛就不怕你。你驯服不了它不说,它发起作来还会连人带犁拖着满山跑,这就叫发了“牛脾气”。所以直到现在,凡性格倔强的人,农村人还是说他像个“抵人佬”似的,说的是那种好斗的大犍子,犟得像牛,所以“犟”字下面就是个“牛”字。
被驯服了的牛任劳任怨,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仍然是“老黄牛”,不辞羸病卧残阳。即便是退役的老牛,也是很值钱的,或牵到市场上去论个卖掉,或请人宰杀后论斤论两卖,光一张牛皮就能卖个好价钱。也曾有个别仁慈的老农怜惜老牛,念它耕作一辈子,一不杀二不卖,硬是等到它寿终正寝之后才恋恋不舍地将它埋葬。
这些是我所知道的跟牛有关的话题。近日读一本杂志,上面说牛都是色盲。怪不得夏天青草满地时牛啃得很欢,冬天给他喂干枯的苞谷秆子、黄豆秆子,它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呢,原来它是不懂得什么色香味俱全的。色盲好啊,分不清青草与枯叶,只管咀嚼,吸收营养,蓄精养锐,少了多少麻烦,省却了许多烦恼。我这个半老古董大概也是“色盲”吧——几乎对女色没多大兴趣。天生近视,再加上如今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性大都打扮成清一色的时髦样,浓妆艳抹,低胸裙袜高跟鞋,真让我不敢正视。工作中免不了会接触些陌生人,男的见几次面就记住了,而女士总是见过好多次面还是认不出来,要么张冠李戴,常闹笑话。这样的色盲也蛮好的,白天安安心心上班做事,晚上躲进山巅小家喝小酒睡大觉,上为老下为小,四平八稳做事挣几个工资,到老也出不了多大问题。
世事变迁,老牛拉车已成为传说,田地不再用牛耕,养牛的人早晚也会绝迹。认不出老黄牛的孩子会越来越多,“犍子”“犁耙”“调牛”“抵架”之类的词汇也行将消逝。但依我的肤浅之见,老黄牛精神并不过时,似乎还是值得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