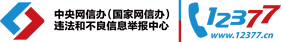云在天边沸腾,像煮开的水。寒光偶尔从青龙偃月的刀刃上游过,一闪即逝。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吹来,掀动刀头红缨飘动不止。一同飘动的,是那美名远扬的长髯。长髯之上,一张枣红色的脸上,凤眼微睁,蛾眉轻戚。在这座山头,他已经像雕塑一样伫立很久了。周仓杵在他的身后,犹如他手里青龙偃月刀,一动不动。那些身披甲胄的士兵,有的站,有的坐,有的斜靠在山坡上,一脸倦容。
风依然不时撩动刀穗与长髯,刀和人一样依然纹丝不动。关平似乎忍不住了,轻轻走到关羽身侧,像在询问,又像自言自语:“怎么还没到,应该来了吧?”
关羽没有回应,甚至连眉毛都没有抬一下,一任晚风吹乱长髯。但枣红色的脸上,明显有了焦灼,眉头拧得更紧。
是啊,数万将士已经喝了三天粥了,粮草再不运来,不要说打仗,可能连走都走不动了。作为主帅,他能不急吗?可是,再急,他也不能动。不然,士气就泄了,军心就乱了。该派的人马已经派了,剩下的只有等待。
天色暗了下来,焦灼的空气更加浓烈,一些不易察觉的轻叹似有若无地飘来飘去。突然,“来了,来了”的兴奋一下打破沉闷。关羽抬眼眺望过去,只见远处山脚下一队运粮人马逶迤而来,迎风飘扬的帅旗上,“关”字依稀。
从此,关羽立身的这座山,就被唤作望粮山。
时光倥偬,1800多年后,当初关羽伫立望粮的这座山,成了我的故乡。即使命运交错,少小便离开这片土地,但不论走到哪里,望粮山的一峰一岭、一草一木,都始终烙印在我心里。
望粮山的地势并不险峻,峰岭起伏平缓有序。在鄂西北整个荆山中,算得上中规中矩。那些山,彼此相似、亲如兄弟,一路络绎不绝。那些树木,枝靠着枝,根脉相系,品种也不复杂,松树、杨树、花栎树居多。一眼望去,仿佛都是一样的山。满山都是一样的泥土和岩石。泥土之上,长都是一样的草木和庄稼。那些土夯的老屋,就分散在这些山岭上,一个院子傍着一个院子,三五成群,星罗棋布,鸡犬相闻。
老屋朴素而谦卑,一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泥土夯起的墙体,厚实而粗糙,散发着淡淡的土腥。屋脊低矮,窗户狭小,若不是土黄的墙体与黛绿的山色形成明显的对比,几乎都难以寻觅。我挥动细小的手臂,推动笨重的木门,发出吱呀的声响,然后一溜烟地扎进屋后莽莽丛林里。
猪圈偎在老屋旁边的坎下,傍着一半山体,砌上半圈石墙,就圈出了农人一年的荤腥。菜园简单,随便在房前屋后刨出几小块地,白菜、萝卜、黄瓜、茄子、土豆、莴笋、菠菜……就随着季节变换在地里交替上场。冬闲时分,父亲会从猪圈里掏出一些夹杂着猪粪的腐烂树叶掺进土里,肥沃田园。然后,再从屋后的树林里扒来落叶垫进猪圈,让牲猪温暖过冬。
小时候不操心生计,对牲畜、蔬菜、庄稼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到是对屋的山林、岩石和那些零零散散传进耳中的关羽的故事很好奇,总想知道,那些山石为什么会长成这样那样的形状,关羽是站在哪座山峰眺望运粮人马到来的,是不是我家屋后的这座山,还是对面那座?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童年的许多问题,找不到答案。
离开老屋旁边的小学时,我也就离开了家乡。那以后,家乡的山岭风物和熟习的人事,都只能在梦里交替叠印。
寒露一过,柿子挂在树上,红彤彤的。一转过屋角,就看见它们在枝叶间炫耀。忍不住嘴馋,找来长长的竹竿倒是对屋的山林、岩石和那些零零散散传进耳中的关羽的故事很好奇,总想知道,那些山石为什么会长成这样那样的形状,关羽是站在哪座山峰眺望运粮人马到来的,是不是我家屋后的这座山,还是对面那座?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童年的许多问题,找不到答案。
离开老屋旁边的小学时,我也就离开了家乡。那以后,家乡的山岭风物和熟习的人事,都只能在梦里交替叠印。
寒露一过,柿子挂在树上,红彤彤的。一转过屋角,就看见它们在枝叶间炫耀。忍不住嘴馋,找来长长的竹杆,伸进密密的树叶,去挑那些早熟透的柿子。再高一点的,只有爬上树才能挑到。好在小时候灵活,爬树不是问题。有时,甚至因为身子小,还能慢慢爬到高高的树梢去摘。
现在,站在柿子树下,头发开始飘白的我,再也难以像小时候那样,赤脚爬上树去。柿子在夕阳下耀眼地红着,我心里却升起一丝怅惘。树还是那棵树,而我却已不是当年的我。转头向老屋望去,过去的那些土墙黛瓦早已不复存在。替代它们的,是一栋栋墙面贴满瓷砖的小洋楼。明亮巨大的玻璃窗反射着远方的夕阳,铝合金的窗框也闪着金属色泽,烁烁映眼。再也不像老屋的那些小木窗,做得厚实而狭小,仅能透过不多的光线。夏季还好,到了冬天,即使白天进屋,也感觉一抹黑,要点着煤油灯才能看清室内。
煤油灯早就不用了。印象中,从煤油灯到白炽灯,再到日光灯,以至现在的LED灯,是一代比一代亮。就像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光明。
现在的望粮山村,是由原来的望粮山、榔榆沟、铁厂垭三个大队合并而成,范围一下子拓展了一倍多,人口却只有1300多人。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少。年青的差不多都外出务工了,只在农忙季节,抽时间回乡帮帮忙。这些年,凭着好政策,老乡们在原来的农田种植之余,发展经济种植和牲畜养殖,生活富足,条件完全改善。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实现了。小时候最期盼的顿顿大米饭,早已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倘若关公带着队伍再来,想必也不会再像当年那样为粮草着急,天天爬上山岭眼巴巴地眺望送粮队伍早一点、再早一点到来。至于洋楼、家电、汽车、手机……城里有的,现在乡村都有。
可不知为什么,在我心里,仍然眷恋着原来的乡村。仿佛,那是心中永恒的念想,寄托着一生难忘的情感。
找不到过去的土屋老宅,也寻不着那时的乡土原味,就去看看风物吧。景是人非。那些山岭,那些树木,那些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应该可以抚慰对故乡的念想。
沿着乡间公路向余家岭行去。林间的路是早先浇筑的,时间久了,好多地方表面都已沙化,毛毛糙糙的。车行上去,一路沙沙作响。余家岭印象最深的,是岭上的水坑。早先,村没有现在这样的自来水,家家户户都要到附近的水井去挑水,然后装在土灶旁的大水缸里。有的人家幸运,家的附件就有沁水井,山间清泉汩汩从地下涌上来,四季不断。而更多的人家,就要去余家岭上的那个大水坑去挑,来去很远,水质也不是很好。
望粮山什么都好,就是缺水。不光望粮山,方圆几十里,都因了喀斯特地貌,蕴含不住水。遇到天干地旱,农田无收,人畜吃水都十分艰难。
车在山间绕行,那些曾经十分熟悉的树木从眼前逝过,还有那些匍匐在地上露出一些嶙峋的岩石,都是原来的样子,感觉特别亲切。一时间,仿佛又梦回少年,无忧无虑地放马山林。
忽然,那棵参天古松闯进眼中,心中顿时一热。停车绕树,不知是古松太老的缘故,还是记忆紊乱的原因,感觉它还是原来的样子,那么粗壮,那么伟岸,那么苍劲。伸臂一抱,和小时候一样,依然难以抱住。反复打量,感觉还是增加了年轮,粗壮了腰身,直径至少一米五开外。伸展的树枝,仿若巨大的华盖,撑出亩余的墨绿,一如树神屹立。
继续向上,是那方水坑。曾经,在吃水艰难的年代,滋养过方圆几十的乡亲。只不过,再见到它,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过去,它就是黄泥地上的一个小土坑,储蓄着天然的雨水,坑不大,应该不过几分地。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水池,周围用水泥浇筑了堤坝,占地也拓展到三四亩。问询附近的老乡,说是为了解决用水困难,政府投资进行了扩建,满足农田灌溉,取名“望粮天湖”。湖的下方,那些沿山开辟的旱地,因为天湖都改成了高标水田,种上了高产稻米。民以食为天,天湖比过去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望粮山曾是茶马古道,南来北往商贾频繁。当年关羽率队征战,多次经过,为这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围绕这些历史经脉,村里修建了许多文化长廊,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信步村道,田边、石上、隧道口,有许多展现古风旧韵的连环画、地雕、浮雕,一如历史浮现,演绎着纷繁复杂的千古传奇。那些桂花、石楠、女贞、紫薇……沿路招摇,装扮着乡村。
作家晓苏是望粮山的当代名人。或许和我一样,离家乡太远,对家乡的情感太深,他的笔下,家乡的油菜坡反复出现。家乡的山水哺育了作家,作家用满怀情感的乡俗俚语书写着家乡。从《松毛床》到《三层楼》,从“廖香”“豌豆”到“花嫂”“自喜”,晓苏的许多作品中,乡土人物往来穿梭,演绎着一个个平凡而又朴实的乡村故事。
其实,家乡的土地并不神奇,甚至还很普通很平淡无奇,可在早已远离家乡的游子心里,却永远那么可爱,那么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