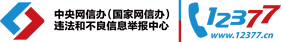那时,爷爷一见我与新养的白狗套近乎,蹲下身摸它们的脖子上的毛,就会虎着脸呵斥我:“别碰它!它又不是咱家从前养的大黄!”
爷爷说的大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没人照顾时的保姆兼玩伴。它忠厚老实,很像旧时地主家俯首贴耳、鞍前马后的家奴。
爷爷去后山撵獐时,它一会儿在前探路,一会儿在后压阵。一跑,一身黄灿灿的毛就抖起来,像只威风八面的狮子。不管回家时,爷爷手中有没有猎物,它都在快到家门时,一阵兴奋的狂叫,引起大家的注目,都以为它立了头功。
奶奶挽着篮子去菜地,它眼尖,一见奶奶经过拐角的苹果树下,它就一溜烟儿地奔过去,扑到奶奶脚边,用它的粉红舌头又舔又亲,甚至两脚离地站起,恨不得亲奶奶的脸,犒赏半会儿没见的女主人。奶奶边笑骂边踢它,劲儿不大。大黄这样一直迎到门口,奶奶跨进了大门,它才到门槛边,伸着长舌头,趴下了。
据说,那时我才一两岁吧。有次爬到大黄旁边玩,不知我把大黄当成了个什么玩具,居然摸着摸着就掰开它的大嘴,大黄不知所措地张大嘴巴,任凭我肆意妄为。结果,我咯咯笑着,竟然把我的小细胳膊一点点伸了进去。大黄哪经历过这场面?它被我弄得难受极了,又不敢闭上嘴巴。当爷爷过来,一见我大半胳膊都在狗嘴巴里,吓得变了脸色。想大喝一声,又马上忍住了。他说,他要一叫,吓着了大黄,它肯定会合上嘴就跑,我的小胳膊肯定就没了!他慢慢走过来,战战兢兢地把我的右胳膊从大黄大张的嗓子、嘴巴里一点点取出来,居然像从灶膛里退根柴火头一样容易。因为大黄也吓坏了,嘴巴张得老大,口水流得老长!
当然,这都是日后爷爷告诉我的。说的时候,带着后怕与感念。
爷爷总说大黄通人性,我也这么觉得。虽然这件事因为我太小而没半点儿印象,但爷爷总喜欢对我、对家人老生常谈。以至于我在一遍遍回味中,似乎又亲眼看到了这件事的始末。
其实,当年它要是喉咙太难受,一口咬下去,也不怪它。谁叫那时的我因无知而对一切充满好奇与无畏呢?谁叫大人们不好好看护着满地爬的我呢?如今,摸摸我健在且长长的右胳膊,我实在该感谢大黄的不咬之恩。
大黄是我们家养得最久的狗。我记事时,家里就有它摇头摆尾的身影。安祥的夜晚,有山风在四野呼啸,突然,墙角传来几声大黄沉稳的叫声,我就安心了,翻个身沉沉入梦。有大黄看家护院,我们都很安心。
它要被卖掉时,我已长大了。
那时我回奶奶家次数就少多了。再见它,它摇着尾巴迎过来,步子迟缓而滞拙,抬头看我的眼神是浑浊的,像一滩死水。但那神情还和从前一样,只是高兴中有一种沉重的忧伤:当年在它身边爬的小丫头长成了个稳重的小姑娘。大黄呢?慢慢变成了老态老钟、不中用的狗。它只有在看到了人之后,才叫几声。因为它耳朵听不见一点声音了。爷爷晾晒在屋旁的药材茯苓被贼偷去不少,它竟一点儿也没觉察到。
别人劝爷爷奶奶杀了大黄,狗肉可以炖一大锅子。奶奶生气地说:
“养了那么多年,它的肉我们吃不下去,吃了会短寿的!”
我记得,每年过年吃团年饭前,奶奶都要把刚出笼,还冒着热气的包子丢几个在门外的大黄面前,还笑着对它说:“你也要过年哦!”
爷爷蹲在一边叭吧嗒吧嗒吸他的旱烟,不吭声。蓝灰的烟雾一腾一腾地将他围住了。过了会儿,他一磕烟锅,说:“卖了吧!”
我也愁得心焦:家里确实需要一条壮年的狗看家,可是不杀大黄,卖了吧,它还不是逃不过被宰杀的命运?
那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狗贩子一脸凶相 ,浑身散发着腾腾的杀气,站在我们的院场里。他恶狠狠地瞪着耳聋眼花、身上黄毛脱落得厉害,变得黄一块灰一块的大黄,像看一块破抹布。良久,他吸了一口气,对爷爷淡淡的说:“得把它弄死了,才行。不然怕它走不动。”那口气,俨然他是掌管大黄命运的判官。
我急得眼泪差点掉下来。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居然冲他嚷道:“不准把它弄死!” 那人瞟了我一眼,没听到一样,扭头对爷爷说:“去找根绳子。”话语里有种不容置辩的力量。
爷爷没说什么,默默地往羊圈方向走去了。我飞快的跟过去,对着爷爷的后脑勺说:“别弄死它!爷爷,大黄不是还帮我们看过羊吗?” 他的眼光停留在角落,我望过去,那是一根牵头羊的棕绳。
我们都愣了愣,仿佛看到几年来,大黄跟在爷爷左右,和他在晨光熹微的时候,放出圈里的羊群,叮铃铃的铃铛在沾着露水的清晨,格外响亮。当有羊乱跑时,大黄就猛地冲过去,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吼叫,那羊就很听话的乖乖归队了。黄昏时分,爷爷还没想到要去把荒野里咩咩叫的羊群赶回来,那羊儿们,就在大黄的一阵尖利、惶急的叫声中,咩咩叫着,跳下后山的土坎和大石头,扬起一路尘土,披着夕阳金黄的余晖,径直奔向羊圈了。它们像是一队纪律严明的兵士,大黄在它们身后,仿佛是个严厉的指挥官。每每这时,爷爷只需要跑过去,把头羊身后拖着的棕绳解开就行了。大黄赶回了羊,也不邀功,就在黄昏的柿子树下,眯着眼静静的趴下了,仿佛它干的不过是职责本分的小事。
要不是好多次我闻声出门,看到这样相似的情景,我真想不到我们的大黄,是一只如此出色的牧羊犬。(我甚至好奇,在荒野和去回的路上,大黄和羊群们怎么交流的呢? )可是,现在,我们就要用以往牵羊的绳子去结束大黄的性命,大黄知道的话,会不会心寒并心生怨恨呢?
爷爷愣了会儿,还是铁青着脸,捡起了绳子,转身走向了狗贩子。药材被偷的余怒也许在他心中还积压着吧。奶奶不在家,我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劝说爷爷,他不回心转意。看看狗贩子那副钟馗一样的黑面孔,我也不指望他会心软。我竟觉得大黄的生死,似乎都跟我有关,可我又弱小得无能为力,急得直想哭。
爷爷拽着我右胳膊,攥得我生疼。我眼睁睁看着狗贩子将绳子系了圆圆的活扣,慢慢弯下腰,对着大黄的脖子套过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想喊:大黄快跑!可是我知道大黄听不懂我的话,就算听得懂,它耳朵聋了,也听不见啊。只见大黄平静地眯着眼,驯良而安详的坐着,就像它每次狂吠着迎来一个客人后,或者把羊群赶回圈后,在大门边那样坐着一样。仿佛它什么都知道,又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坦然接受眼前的一切安排。
多年后,我在书中看到“引颈受戮”这个词,一下子就想到了我们的大黄。对,它就是那种引颈受戮的样子,不挣扎、不反抗、不哀怜,平静而坦荡的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种誓死捍卫的忠诚,让我多年后,想起它时,仍想落泪。
绳子在那狗贩子手里越缩越紧,大黄的四肢徒劳无功地在泥地挣扎了几下,腾起一小片黄灰。它闭紧了眼,喉咙发出一声痛苦的呜咽,低沉、含蓄,凄楚,像是对这世界发出的一声沉痛的告别。我只觉得,那绳子好像也勒在我脖颈上,让我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爷爷的手伸过来,死死地捂住了我的眼睛,我分明感受到他那粗糙的大手在微微颤抖。
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响起:“别弄死它,我们不卖了!”是奶奶!原来她去四奶奶家串门回来了,刚好见到这一幕惨景。
狗贩子一听,忽的松了手,爷爷也松开了捂我眼睛的手。大黄缓过来一口气,张开嘴,大口大口的喘气,睁开眼看了看周围的我们。然后, 它慢慢地耷拉下了脑袋,又一歪,躺下了。我们以为它死了,跑过去看它,凑到它鼻头的手指,分明感受到它还有若有若无的呼吸,我才松了口气。它静静地躺着,睁眼看了看我,昏沉的眼眸忽然亮了一下,又合上了。仿佛刚才的跨过鬼门关又回到这世界,不过是它做的一个有惊无险的梦而已。
我蹲在它面前,一边心有余悸,一边幻想:它要是会说话,会跟我说点什么呢?说我小时候差点噎死它的囧事,说它在阳光下的山林追逐羊群奔跑的快乐,还是叫我不要责怪老主人的狠心?可是,它什么也不会说,狗的天性就是供人驱使,生死由人。
我们赔了许多不是, 狗贩子愤愤地走了。奶奶责怪爷爷糊涂,爷爷也不恼,竟笑呵呵的,忙给大黄端去他吃剩下的半碗稀饭,一瓢土豆。我去看它,蹲下身子摸它时,它偶尔会伸出舌头,舔舔我的裤脚和手掌。
一阵冷冷的秋风吹来,它又躺下了,眯缝着眼睛,喉咙里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在絮絮叨叨中追忆生平。
半个月后,大黄不吃不喝,躺着就再也没能醒过来。
爷爷将它埋在竹林深处,那里竹子长得密不透风,像一片绿色的锦幛。
从那以后,每当我从竹林中的小径走过时,总觉得隐隐听到了大黄的一声低低的吠叫,回头听,只有头顶的竹叶,在沙沙作响。

保康微信平台 微信号:baokang0710
编辑:孙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