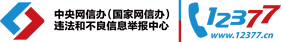岁末年初,于城居者而言,却常常怀想起乡下的冬来。
乡下的冬,如一幅画,是一层一层展开的。立冬是一条线,冬至又是一条线,到了小寒,界限就更明显了。正所谓“小寒已近手难舒,终日掩门深闭庐。”
小寒的乡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田野山川,河流岩石,变换了冬的冷色。有霜凌在清晨的草丛上闪亮,渐渐地,盎然的山景疲软下来,门前的地里裸露出一截儿一截儿的褐色,嗅嗅,秋腐的味道渐渐消失,土地的芳香弥漫开来,有一种亲切随风而至,冬天原来可以如此清新可人。
站在小寒的门槛上,瞻前,小雪大雪,冬景自秋黄深处姗姗而来;顾后,雨水惊蛰,春暖花开,时节又急火火地向夏而去。唯有小寒,不疾不徐,踏着自己的节奏前行,有雪无雪,都将日子冷静成一年中的极致。有雪呢?更好呼应了节气,冰封雪飘,聚集,收纳,沉淀,消融,洁白的世界,那么纯粹,那么清新,澄澈而明丽,看不见浊污,也覆盖了鄙陋,天地间,冰清玉洁,只遗下一股清朗的气息。
乡谚云:“三九四九冰上走”。说的正是小寒前后的天气。当然,冷到极处,也是在预告天下,周天回阳,四季即将朝暖。自古物极必反,阴阳互化,天道亦然。于黄河以北而言,小寒虽带了一个“小”字,却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小中藏大,冰衔日月,雪覆苍山。只是到了南方,小寒才名副其实,小寒小冷,大寒大冷。古云: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也有一年年的大小错位,或混为一体的,年份的异动,气候亦改常态,推究起来,也符合山川物候微变之理,因此,民间素有“小寒胜大寒”之说。
少年的岁月里,分不清时令节气,但却记得春头腊尾,雪一直飘下。立冬之后,便常常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让人分辨不出小雪大雪,还是小寒大寒。那些年的雪,出奇的大,冰凌的路上,绿莹莹的,晃人眼,走在山野小径上,大人们非得穿上脚马子,或者鞋底绑一根稻草绳或是包一匹山棕叶。
记得去往外婆家的路上,我不敢稍有顽皮,父母牵着拽着上赶着,新买的浅口胶靴,只能老老实实地套进母亲的鞋印里,一步三滑,小心翼翼。那踩出的一溜鞋纹,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起伏有致,如波似浪,远观之,则像如今覆了薄膜的山腰茶垅。我们几兄妹一边探路,一边笑闹,飘舞的雪花落进脖领子,冷沁沁的,沁人心脾,不由得缩短了身子。惊叫一阵之后,呵着气,捂着红彤彤的脸颊,然后继续前探,继续尖叫。
母亲说,小寒大寒,冻成一团。笑声跌落的瞬间,记忆定格在了山间的雪地上。从此,我知道了冬天最冷的是小寒和大寒。也从此,寒冬的雪在我心里一直飘飘荡荡。
早年读《逸周书》,知有“三候”之说:雁北乡,鹊始巢,雉始雊。古人早把物候气象的脾性摸透了,大雁北向,喜鹊南巢,野雉四面觅偶。“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鹊巢新筑,是个回阳的风向标,一切物候都有了新的动向。
时令就这样,该行则行,该止则止。雨几滴,风几缕,空气中的寒意就淡了,再往后,立了春,就更浅了。
我从小喜欢小寒,心里是藏了小九九的。小寒一过,这“年”就在手指头上掐着了,招摇的年节摆动着多彩的腰肢向我款款走来。要知道,缺吃少穿的年头,过年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诱惑不仅仅是母亲烹饪的一桌子“十碗八扣”的年夜饭,还有外婆围裙兜兜里香喷喷的杂糖芝麻饼子。
听北方的朋友说,他们早年的小寒,已在写春联、剪窗花、看冰戏,忙着买年画和彩灯。与南方相比,北方的冬天冷而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忙年闹年。要是生长在北方,我也会坐一辆马车、听着清脆的鞭声,走在赶集的路上。
中年以后,我还喜欢小寒,那是因为小寒让我多了份冷静与平和,也多了些内敛与谦卑。一年结束,以寒为界,可以划个句号,封藏住往日的快意和失落,而一元伊始,又将春暖花开,怀揣着希冀,打理好一日三餐,向着平凡的日子,一页一页,朝前翻过篇去。
喜欢小寒,还因为小寒莅临的日子,有书酒相伴。
十八岁那年,我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一个人,四个年级。九月开学,我们坐在操场上,一个大孩子领着一群小孩子,迎着朝霞晨读,琅琅的书声惊醒了一湾的炊烟。夕阳西斜,孩子们都回家了,我会拎上一把锄头,去校田里锄草。入夜了,一盏煤油灯成了我最好的伙伴,备课改作业,听窗外秋雨沙沙,也静静地读书、听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
时间真快,一晃就到了小寒,到了年跟前。
乡村的冬,杀猪宰羊,山弯弯里一片欢呼。放学了,总有学生受父母委派,拽着衣袖,邀我去家里做客。旺叔家的蒸肉,是地道的土家大木格子,一格蒸肉四斤多,外加衬垫的洋芋南瓜,满满一大格。热腾腾地端上桌时,中间放一碗葱爆血花,满屋飘香。
酒早预备下了,旺叔家的酒,地道的苞谷老烧。走进堂屋的时候,云伯正跟旺叔打赌,一碗肉一杯酒,碗是兰花海碗,杯是三两白瓷杯,二选一。旺叔选了酒,不承想,云伯是个饭量子,居然吃了半格蒸肉,折合四海碗。旺叔二话没说,连浮四大白,下桌子的时候,虽然连路都走不稳当,但他却把云伯吃醉了,一连三天人事不省,后来村里就流传开了云伯“醉肉”的故事。
原不知道,村酿的酒,劲那么大,小呡一口,喉咙里竟像着了一团火,但就是那酒,乡亲们却喝得有滋有味儿,大口的酒,大块的肉,一屋子的人,把爽朗的笑声抛上了云天,也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乡下男子汉的豪放与粗犷。
窗外,雪一直在下。月上中天,我才走在回校的路上。茫茫的雪地里,留下了我歪歪扭扭的足迹,那是我第一次酒后的佳作。
那以后,无论大餐小聚,只要端上杯子,我都会想起那个雪落村湾的月明之夜,想起父老乡亲的满怀热情。
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却从不知道酿酒的工艺和流程。今年春天走了一趟保康的清溪河,在尧治河酒厂,工人们正在忙活着,拌料、上甑、蒸煮、取酒、收糟,一屋子的蒸汽,一屋子的酒香。研发部的负责人告诉我,相比于浓香型,酱香型的酒工序更复杂,工艺要求也更高,尧治河2018酱香酒,就必须严格经过“12987”。我知道,那是行家的口诀,意即“一年一个周期、两次投粮、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前有制曲,后有勾调,如此繁复的工艺之后,才进入五年的窖藏期。因此,我比较了酒的清香和浓香之后,知道尧治河的酱香是以其独特的古法酿酒技艺而著称。
走出车间,场院里那些一吨重的酒罐,如将军布阵一般,成百上千地密密陈列在阳光之下,陈列在清溪河畔,似要随时出征远行。至此,我才知道,窖藏之前,须得在高温与恒温之间转换,看来,刚刚看过的七个酒库里那一排排的酒罐,都是从场院里转移进去的。正所谓,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这样的阴阳调和,符合中庸之道,顺应了一年的春秋四季,也丰润着我们的五脏六腑。
好日子好酒,是最能动人心魄的。回家的时候,我把带回的“尧治河”酒,一瓶送给父亲,一瓶送给了二爹。
父亲醉心于酒,亲密了一辈子。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年轻时喝酒,重友情,讲义气,酒喝得豪爽,也醉得厉害。问父亲,何至于斯?父亲的理由是,乡里乡亲,经不住劝。何况酒是喝的人缘,喝的感情,喝的乡谊,酒喝得好,利人利己。
十里八村,父亲有些名望,乡亲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总爱和父亲唠唠,几杯酒下肚,人就掏心窝子。亲朋絮絮地说,父亲静静地听,这一听,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实事求是地说,父亲的酒量,在村里排不上号。但父亲的直性子,又不容他不端杯子。一座村子,人多,事也多,红事白事,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出,无酒不成席,于是,父亲也就常常醉在月光里。
父亲现在喝酒,喝得优雅,也喝出了讲究,夹一块牛排,尝尝,放下,笑眯着眼,端上小杯,轻轻嘬一口,然后再夹起牛排。父亲喝酒,自己给自己限了量,八十多岁的人,他学会了品味生活。
看着我带给他的酒,轻轻拧开手中的瓶盖,一闻再闻,对我说:“尧治河”,这酒好香,品质不错,还是第一次见到呢,真是藏在深山人未识啊!父亲一边闻香,一边笑着说,我得珍藏起来,留着细细地品。
村里真正喝酒喝得讲究的,还是隔壁的二爹。
每次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二爹一定要把我接到他家吃顿饭,喝杯酒。二爹喝酒,从不用大杯,主菜上桌的时候,他会找来一只蓝花瓷壶,老式,曲嘴,出壶如注。两只蓝花瓷杯,小喇叭口,装一两左右,斟到八分满的样子,停住,然后招呼我入席,爷俩儿一边浅斟慢饮,一边等待二妈后面的炒菜。
二爹喝酒,姿势优美。手里的筷头一伸,表示“请”菜。手指捏着小杯的把儿,轻轻放到唇边,“嗞儿”地一声,呡上一小口。尔后用筷头点几点火锅,里面有香喷喷的羊肉或腊蹄子,而他自己则夹一颗炸得酥黄的花生米,送进嘴里,细细咀嚼。
喝完一盅,再斟上,依然八分满。二爹劝酒很殷勤,也很周到,轻言细语,一请再请。谦谦君子,这是我对二爹酒桌上的评价。所以有了这样的好酒,我会第一个想到二爹。我能想象得出,他打开我这回送他的“尧治河”时,那一份欣喜,那一份庄重。
父亲说得没错,好酒得细品。
小雪那天,我带了一瓶“尧治河”,约了鹏哥,还有明叔,找了一家叫“翘牛脚”的小酒馆,就着火炉上新涮的牛肉,一边浅斟慢饮,一边叙旧话家常。窗外雪花飘飘,室内炉火暖暖,我们喝得很随意,几十年的交往,酒只是个由头。但有了这酒,心里就温暖起来。隔了火炉,时不时地碰个杯,氤氲的热气中,人生的酸甜苦辣就在杯中荡漾。他们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回趟老家不容易,约齐一次更不容易,所以,那天的酒,我们喝到很晚才散去。
欢饮小酒的夜晚,很美。回到家的时候,妻迎上来,很体贴地帮我脱下外套,我一把将她拥进怀中,突然有了醉意。这样的夜晚,是需要说点酒话的,平日欲言又止的亲昵,这会儿,或可激荡而出,呼出的酒气,哪怕喷洒得怀里的女人一头一脸,她的心也是温暖的。当月亮偷偷隐去山坳的时候,窗外只剩下了一地银白。
前天,鹏哥从北京打来电话,笑吟吟地问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欣然接话,红泥小火炉,才开了一瓶“尧治河”,快来,快来!说完,电话里传来两人畅快的笑声。
窗外,真飘起了雪花。
“雪点梅花霁后妍,屠苏酒饮庆新元。”再过些日子,窗外看到的就不是雪花,而是沙沙的春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