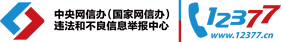一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便是年,腊八粥,吃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这是一首广泛流传的关于年的童谣,也就是说过了腊月初八之后马上就会迎来春节,民间要开始准备热热闹闹地过大年了。
事实上每到腊月以后,一向严厉的母亲便对我们格外温柔慈爱起来,比方说打碎一个碗、说错两句话、在哪儿闯了一点儿祸事等,她自然不予计较。但总不好去犯了她的禁忌,像“死亡”“倒霉”这些话是万不能入她耳的,要是不小心脱口而出让她听到,照样免不了一顿狠狠地责骂,母亲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天地万物心存敬畏,她觉得“年”是神圣的存在,任何不好的事情、不吉利的话语都是对年的亵渎。
腊月二十三是个重要的日子,“打塘儿灰”(打扫厨房灰尘),每年天不见亮母亲就从床上起来,灶屋(厨房)实在太高够不着,母亲用长竹竿把梢头绑上几枝竹叶举过头顶,对着瓦片、檩条、墙角旮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细打扫,那些蛛网、灰尘吊子纷纷落到地上,拾掇清理一番后,模糊不清的瓦片、烟熏火燎的墙壁顿时也明亮可人起来。二十五六动炸货,二十七八篜馍馍。那些天里,母亲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忙碌,那个时候受经济条件限制,基本没什么东西可炸,但是打豆腐、熬麻糖、蒸馍馍,拾掇凉菜扣碗子(蒸篜肉)这些东西还是必不可少的。
母亲做的一道凉菜十分新奇有趣,就是把猪头清洗干净放上调料卤制剔骨,趁热加上事先剥好的核桃仁,用纱布包裹后捋平放到两扇石磨之间自然挤压,待到一定程度取出,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方形片状上盘,核桃仁经过压实后嵌进肉里面形成一种独特花纹,此菜名为“压肉”,看着精致养眼,入口滑嫩劲道,过年待客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打豆腐和熬麻糖过程细碎烦琐,尤其熬麻糖是个技术活儿,时间火候要到,若是差了一点儿工序,忙碌几天有可能是前功尽弃。那些天里,母亲通常是忙得脚不沾地,身影像陀螺一样旋转,灶膛里白天黑夜总有熊熊火光燃烧,父亲在旁边打下手,常常夜半醒来,听到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父亲母亲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便会觉得莫名心安,迷迷瞪瞪一会儿便又沉沉睡去。
等到七七八八准备得差不多时,转眼也就到了腊月三十这一天。
大人望种田,小儿盼过年!一大早上,我们精神抖擞,两个姐姐协助母亲张罗厨房事宜,我和哥哥包揽所有房间卫生,楼上楼下打扫得一尘不染,所有桌椅摆放整齐,每个房间张贴的年画也得擦拭整理,尤其堂屋不能马虎,破损的、太过陈旧的,都需重新更换。小哥站在凳子上拿着画在墙上比画,我到下面指挥“往左,往右,不行不行,高了,低了,在上一点点儿,好、好,这回可以了……”
那些鲜艳精美的年画是我和哥哥用心挑选的,有拖着长长白胡子、拄着拐杖眉开眼笑的老寿星,有猛虎下山图、各种山水画,其中我最喜欢那张《天女散花图》,因为老是听到奶奶煞有介事地说:“某年某月某日,天上会开天门,到时会有大量金银珠宝,奇珍异玩从敞开的天门里源源不断往下掉,只有有缘人才能看到。”我盼望自己是那个有缘人,我总是把图画上漂亮的天女姐姐和这件事情联想到一起,期待有朝一日,能亲眼见证美丽的天女姐姐臂挎花篮、素手纤纤、皓腕轻扬,许多花瓣从天空纷纷扬扬往下洒落的神奇情景。
要贴对联了,我端着盆子,盆里是姐姐用苞谷面熬制的黏稠的糨糊,我拿一把破刷子沾满糨糊递给哥哥,他往门框刷上两刷,把对联扶正贴好。对联是由父亲亲笔书写,父亲写一手好毛笔字,每逢年关,方圆十好几里地的人都拿着红纸到我家求取父亲的对联,我小做不了别的事情,牵对联的任务非我莫属,常常椅子上搭的、桌子上挂的、地上铺的,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对联,满屋飘散着浓浓的墨香。
对联贴好后,满脸络腮胡子,豹头环眼的尉迟恭、秦叔宝各自手持兵器,威风凛凛地往两个门扇一站,年的气氛便又浓郁了许多。
吃团年饭是过年最为关键的环节,我们那里习俗通常是为晚餐,我们把母亲忙活一天做好的各色菜肴陆续往桌子上端,蒸好的馍馍,招待客人要用的瓜果食品样样不落,一切准备就绪后,母亲虔诚地往神龛里上两炷香,双掌合拢,拜了几拜,口中喃喃有声,一是恭请逝去的祖先们回家吃饭;二来祈愿天堂的祖先护佑后辈子孙多福多寿,无病无灾。为了避免惊扰先人,所有闲杂人等一律回避,不得出声儿。我躲在门后使劲睁大眼睛,伸长脖子看向外面,努力想要捕捉点儿什么,可是除了黑漆漆的夜什么也没看到,就连树枝都不曾动摇一下。
大概十来分钟后,我们鱼贯走向饭堂,奶奶、父亲母亲、四个哥哥姐姐和我,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刚好圆满,父亲、奶奶坐上首,母亲在左,我坐下首,作为家里的核心人物,父亲先来一段开场白,然后我们轮番敬酒,我端起酒杯,一敬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二敬父亲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再敬母亲任劳任怨,养育我们艰辛。照样,父亲母亲也会回礼,叮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顿热热闹闹的团年饭吃完,父亲已是微醺。
两盆旺旺的炭火寓意来年日子红红火火,父亲坐那儿守财,母亲还有大事要做,她找来马灯点燃,来到院子那棵苹果树下,那棵苹果树是我此生见到的第一棵苹果树,也是唯一的一棵,不知道是不是水土气候的原因,它完全就像发育不良的少女,干干廋廋,叶子发黄,结出的苹果也是又小又酸,树干还喜欢生虫,那些白白胖胖的虫子聚在一起啃咬树干,树皮像锯末一样掉落。母亲把马灯拿在手里围绕树上生虫的地方转圈儿,嘴巴念念有词:“照啥子?照毛虫,照死了吗?照死了……照啥子?照毛虫,照死了吗?照死了……”据说同样的话语要重复七遍才有效果。
茫茫夜色里,母亲打着马灯,我们簇拥着母亲,走向一棵又一棵果树……
二
父亲母亲围着火盆守岁,两个哥哥在外面淘,他们把手腕粗细的鞭炮放到地上,用破洞的搪瓷盆子盖住,然后点燃,发出“嗵”的巨响,我吓得不行,赶紧跑到屋里用被子紧紧堵住耳朵。
夜太深了实在挡不住困意,我回房间去睡觉,哥哥们精神头儿十足,打算通宵不眠,他们在院子里玩冲天炮、放花筒、玩烟花,那种像铁丝一样的烟花燃放起来不会发出半点儿声响,灿烂夺目如正当盛开的金丝菊,我很想亲自尝试一下,奈何慑于冲天炮的威力,只能作罢。
阁楼上,大姐就着晕黄的灯光在梳头,一支花筒拔地而起,“嘭”地在半空绽放开来,从瓦缝里倏忽钻进许多色彩缤纷的小星星黏附在大姐乌黑油亮的发丝上,“看啊!看啊!”十八岁的大姐嚷嚷着,激动地不能自已,椭圆的鹅蛋脸飞上两朵娇羞的红云,她坚信那是神仙爷爷送给她的新年礼物。
当天边露出第一抹鱼肚白的时候,我家门前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堂哥把头磕在门墩上咚咚作响,高声大嗓地喊:“大爹、大妈,我给您们拜年啦!”
父亲穿着一件崭新的黄色军大衣,红光满面,几步从屋里跨出来,一把扶起堂哥,拿出事先早已备好的柿饼、爆米花、糖果、瓜子让堂哥吃。
我按捺不住雀跃的心情,早早换上新衣服,拿着塑料袋,去给几个婶婶拜年。庄户人家勤劳,大年初一都不肯歇着,路过一处牛圈时,看到东边爷爷手上拿着钉耙在往外面淘粪,我赶紧甜甜地喊了一声:“爷爷,我给您拜年啦。”奇怪!并没得到应有的回应,东边爷爷那张本就黝黑严肃的脸上越发阴云密布了。
不过这些丝毫影响不到我的心情,我加快脚步,兴冲冲地往婶婶家跑,一圈下来,衣服和荷包,塑料袋里鼓鼓囊囊全是零食,并非我贪婪不懂礼貌,农村人本就朴实,在她们观念里,送出去的东西绝对没有往回收的道理,要是不吃只能自己带走。
在家族中,奶奶年龄大、辈分高,初一这天,后生小辈都来给她拜年。
初二那些出嫁的姑姑们,还有远房亲戚都来了,整整几天,我们家欢声笑语,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小娃子们像吃了兴奋剂,逮着空子蹿东蹿西,钻进钻出,不管犯多严重的错误,大人们也只是一笑而过,母亲说猪狗都有三天年。何况孩子,不能责罚,不能打骂,天大的事情,也等年过了再说。
初五初六后,客人渐渐稀少。
过了初七八,臭豆腐,老豆芽,就算是有零星客人,主家再也拿不出丰盛美食来款待了。
正月十五赶毛狗(狐狸),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毛狗是什么东西,在想象中,应该是白色的,脸窄而小,嘴巴耳朵尖尖。
傍晚时分,母亲到竹园里搜罗枯枝败叶,还有往年清理竹园时砍倒的竹子,一并抱到空地上,拢成大堆点燃,传说竹子燃烧时发出清脆的炸裂声,能把狐狸吓跑。
刚开始火还很小,慢慢地风借火势越燃越大,赤红的火焰升腾而起,像凌空飞舞的火凤凰,我站得远远地不敢近前,母亲守在那里,时不时拿根棍子拨弄一下火堆。红红的火光映照在她脸上,母亲的脸是那样坚毅而又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