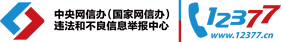广场舞90年在大城市开始流行的时候,河沟村正值不惑之年的牛根叔还在河岔边,左手扶着犁,右手扬着鞭子跟在两头黄牛后头,耕他那只有一晒席宽的地,晒得黝黑的牛根婶,在一脚多宽的田埂上用木根戳了眼儿,是在种黄豆。把这一小块地的价值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居民沿河而居,稍微有些土脚的荒滩在大集体时改成了水田。山上扒得住人的荒坡都开成了旱地,就这人均也不足一亩,河沟最窄处捡个石头随便一扔,摔得过河,老百姓勤扒苦干。河沟村最大优势隔县城近,典型的城边村,但是人多地少,都地里刨食解决不了温饱,大部分出门打工,一些在家做小买卖,搞建筑,会赚钱。牛根叔的瓦房变成了三层小洋楼,腰里别的旱烟袋变成手里的过滤嘴时,背也驼得跟犁辕样,两头弓。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发展,广场舞也流行到了村东头以前集体的晒稻场,现在种地的少,该征收的征了,荒的荒了,水田起了旱,稻场也成了舞场。
牛根叔的儿子在外安了家,女儿嫁了人。三层小洋楼也没留住子女对大城市的向往。偌大的房子显得空荡,也就过年子女回来那几天热闹下。牛根婶年轻晒的肤色至今也没退,依旧咖啡色,但背没驼。近几年连续剧也不追了,跟着村里的一群老太太们迷恋上了广场舞,牛根婶子年轻时种地是一把好手,老了跳舞也下得力,吃得苦去学,三九天上凌都不缺席。舞瘾大,一天不扭两下浑身跟长了跳蚤似的不舒服。广场舞刚流行进来时,牛根婶除了现场去学,回来还对着手机看视频学,有回牛根婶去菜地里掐紫菜苔,突然想到了一个跳舞动作,就在田埂上把这个动作试做了一下,这一做不大紧,把脚脖子崴了。牛根叔帮忙擀了半个月酒火才好断根。
跳着跳着,矛盾便跳出来了,有时候音响开得映山,附近的小儿,升学的学生受到了影响。跟广场舞队提过,管得三天两早上,声音又大起来了。理由是声音不够大的话,气氛就不到位。为此,牛根叔没少提醒他老伴儿不要老了,还搞一些让人讨嫌生厌的事情。没成,遭到牛根婶回怼他。“你看我要不是天天在舞场里蹦跶,背也驼得跟你差不多。”牛根叔听完,把手里的过滤嘴狠狠地抽了一口,两天都没帮牛根婶择蒜苗。
跳着跳着,显得专业起来了,配上了道具,统一了服装。准备把广场舞跳出河沟村,去别的村表演。老太太们一到点换上统一的服装又去集合了,牛根叔的孙子隔得远,也没个唠叨的人,依偎在火笼屋的沙发上,腿上的狸花猫打着呼噜,拿着去年儿子才给他买的智能手机听他的花鼓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