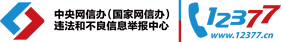谷黄时节,我坐在小城的书房里,仿佛又听见乡下的谷子在歌唱!那簌簌的声响打着节拍,惹得我诗思萌动,于是便在朋友圈贴出一首题为《龙潭河的稻子熟了》的小诗——
从窑岭沟直到仙姑庙
笸箩一样的梯田环环相扣
整个龙潭河,成熟的稻子叠出
层层锦盒。绚丽的金
气跑太阳的傲骄,逐走
秋的萧煞
如挥斥方遒的长者,一群麻雀
站在阳坡岭的乌桕树上
叽叽喳喳,肆意
指点丰歉。我和我的父老乡亲
弯腰躬身,在一块又一块笸箩一样的
梯田,与谷穗谦卑
谈判
我们的腰足够弯到稻谷的
根部,汗水要有汗透衣服的
额度。不然就感动不了
谷子,就不能
顺利将谷粒
娶回家
有朋友看后在微信朋友圈里留言:“你老家有水田吗?”我回复道:“有。十几个水田呢。”只是我没说清楚,十几个水田其实像笸箩一样,斜放在河边一座山坡的尾巴上,总计才一亩多地。地方叫窑岭沟,虽然隔那条叫龙潭河的小河不远,灌溉却用不上河里的水,靠的是山坡一左一右两条小沟里流出的山泉,俗称“冷水田”。
自从父母相继去世,我从小镇调到县城以后,我已经有十几年没在窑岭沟的水田里插秧、砍田边、锄秧草、割谷子了。前年回老家走亲戚从窑岭沟经过,我专程去了看了看那十来块水田,水田里柳树已有茶杯粗细,而且到处留着牧过牛羊的痕迹,昔日的粮田俨然成了牧场。然而我的思想意识总能够和农事同频共振,每到一个节气,总会想起秧苗成长、稻子成熟的那些事来。而且,时间越弥久,意识里的那些场景越来越清晰,就仿佛我根本没有离开乡村,没有离开那些稻田、那些稻谷。
在我老家的那个两坡夹一河的山村,水田是很稀少的,优等的水田更少。小时候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当年土地下放时,父亲不像别人一样,去挑选那些隔河近的河水田,反而要了这十多个水田合起来才凑够一亩多的冷水田,直到后来见到那些河水田不断被洪水冲刷,最后,大部分河水田成了沙滩以后,我才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远见。后来,一些水田减少的农户开始垂涎我们家的水田,借村民小组调整耕地之即,撺掇组长要将我们家的水田分几块出去,虽然父亲强烈反对,但最终还是经不住组长、村主任他们口里的“政策”,最下面的两块水田最终被划给了别人。父亲像割了自己的肉一样心疼,最后又带领我们一家人在旁边的沙地上造出一块新的水田来。
相比在旱田里种玉米、麦子和豆类作物,种稻谷要复杂多了。在农村长大的人们大都熟悉,种稻谷首先要育苗,而后插秧,再到大田管理,最后收割。记得最初育秧很简单,开春天气变暖之后,先整出一块“秧母田”来,直接将谷种撒在里面,等秧苗长到四、五寸高的样子,再把它们拔出来,插到大田里。后来推广农业新技术,换成旱育苗,先将小秧苗育在旱地的小畦子里,待长到一、两寸的样子之后,再移植到秧母田里,最后再插到大田里。在儿时的记忆里,育小秧是很枯燥的事,秧母田被划成畦,插小秧的人搬把椅子,每人一小畦,面前一盘小秧,一株一株密植,一天下来,不仅腰酸背痛,还低得头发痛。而接下来大田插秧就轻松多了。插秧时,往往是父亲负责运输,他把拔出来的秧苗扎成小把,挑到大田里,隔几步抛几把,刚整理过的水田像镜面,映照着蓝天、白云,再加上扔下的秧苗,一切那么清新。我和弟弟则在母亲的带领下,像模像样地一步一后退地插着秧苗。后来我读诗读到“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时,便愈发对诗里描述的情景充满着无限的亲切感。
稻谷的丰歉取决于大田管理。大田管理包括放水、施肥、锄草、治虫、砍田边等许多程序。前面说过,我们家的水田靠两条小水沟灌溉,用水很不便。为了保证足够用水,父亲放倒几棵大柳树,用斧头在柳树上砍出一长条水槽来,而后把这些砍成水槽的木头一根一根搭起来,把水从沟口里接到第一个水田里,第一水田里水满了,再流到下一个水田,以此类推。由于水槽很浅,一把树叶就能把水隔断,有时还得防备放牧的牛群碰翻水槽,阴雨天还得提防涨水冲翻水槽。我们家在半山腰,每天得有人往返七、八里路去检查水路。通常是父亲白天忙完旱地里的活以后,傍晚赶去检查。我们放假以后,便常常在白天借口检查水路,下河去洗澡。尽管是这样,父亲仍然很满足,因为我们不必像种河水田的那些农户们那样,半夜排队放水,也不必因为与人争水而引发冲突。
秧田锄草也是一件很有趣的劳动。秧田锄草一是锄稗子,二是给秧苗松根。起初我们不认得稗子,母亲便说,你们看到比谷秧子高的便是,掌握了技巧,很快我们就能挑出了许多稗子来,心下便有了很大的成就感。给秧苗松根不需要像在旱地薅草一样弯腰,只需要站着,用脚将泡得松软的泥土给踩松,把那些低矮的水草给踩到泥土里面,说是锄草,但对于调皮的孩童来说,就像玩水一样。但我们干活总是很毛糙,一些不到位的地方都得父母在后面返工、补火。尽管这样,父母下田时,还是任着我们去疯去闹。秧田锄草有趣,还在于休息时间我们可以下河。在田头吃过午饭后,父亲便要在河边的柳树下小憩一会儿,这段时间对于我们兄弟来说,是黄金娱乐时间。我们打着赤膊,先在河里垒石,拦起一个水潭,而后便在里面“扑腾扑腾”来一番“狗刨式”。有时,父亲也会在头一天晚上,教我们用作业本上的订书针做成钓鱼钩,第二天午间休息时,我们便演绎一番“蓬头稚子学垂纶”,居然也有钓上来的;有时,嫌钓鱼太慢,父亲便教我们选择一处水潭,在上游把芭核桃树叶砸烂去“毒”鱼,或者用锤子砸鱼。那些劳作之余的娱乐,是如今我们的下一代无法经历、也无法体会到的乐趣。
打药治虫是技术活,我们插不上手。砍田边会时不时撞上蛇和马蜂窝,父亲也基本上不带我们去冒险。那时,生态环境还不是很糟糕,父亲砍田边时会经常捡到乌龟,乌龟常在水田埂上打洞,造成稻田失水。父亲对乌龟恨之入骨,捡到它们,就像扔石头一样扔到河里。有一次,父亲捡到一个很大的乌龟,舍不得扔掉,便把它带回来,在龟壳边上钻了个洞,用铁丝拴了一个环给我们玩。晚上我们用绳子将它拴在场子边上一根木杈上,第二天起来,却发现只剩下半截绳子——半夜里,不知道乌龟怎么弄断了绳子,溜之乎也。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两天后,父亲又在水田边上发现了它,居然还拖着半截绳子,不知道它是怎么又回到那里的。后来父亲听人说,街上有人收乌龟,而且乌龟肉吃了大补,隔年再去砍田边想捡几个乌龟时,却一个也没碰到,不知是乌龟未卜先知跑了,还是被过往的人给捡走了。
转眼到了秋天,相继成熟稻谷成了河沟里的主角,人们开始相互商请着割谷子。在记忆里,插秧、锄草等劳动都是各家各户各忙各的,而割谷子却像是一种神圣的集体仪式。那些天,每家每户都换算着日子,与左邻右舍商请着换工、请工,定下日子后,男人上街赶集,打酒、买菜买面条,女人在家蒸包子、煮腊肉。这个季节,一入村子,处处酒肉飘香。割谷那天,前来帮忙的人们一大早带着镰刀、背篓、抬着板仓来到田头,主人家早把煮好面条、热好的包子、沏好的香茶、切得细碎的旱烟都搬到田头,大家席地而坐,过了早便下地,有的割谷,有人用板仓脱粒,有的扎稻草,有的装背篓,很快,一背篓又一背篓的谷子背回了家,屋檐下、堂屋里,堆满金灿灿的谷子。收完了这一家,再收下一家,白天,小河上下人声沸腾,热闹非凡;晚上,每家每户的场子里,风斗扬谷的声音响成一片。那场面,那情景,比过年还要热闹。
那个时候,在老家,吃“粘米”(当时老家人称大米为“粘米”)是件很奢侈的事,哪家一天能吃两顿大米饭,便被称作是“好过的家儿”。我至今记得母亲曾给我讲有一户人家,晚上把谷子收回了家,便迫不及待地用柴火锅将谷子炕干,第二天一大早,用石磨推去谷壳,早上就用新大米做了一大锅干饭。母亲讲这事,含有揶揄的成份,我后来回想这个故事时,体味到的却是那家人吃新大米饭的那份享受与愉悦。
父母与黄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最后也毫无悬念地回归了黄土。村子里的老一辈,有的相继故去,有的进城跟了儿子。而我们的同辈人,有的上学、参军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打工长期不回来,有的搬迁到了外地,大都以各种方式离开了田地,离开了故土,田地逐渐荒芜,村子逐渐冷清了下来。种田、收稻谷,这些劳作的场景,永远定格在记忆里!
在小城的书房里,我敲打下这些朴素的文字,虽然对村庄、对稻子充满了怀念,但我知道,那片天地我回不去了,村子明天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那些让我魂牵梦绕的稻子,大约永远只会在我的文字里,唱起那些悠远而朴素的歌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