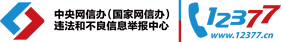我在一场凄惶的梦里醒来。心里的酸涩像青桔泛着饱胀的汁水。我走在故乡的老路上,不,已经算不上是老路。这条路,我许久不走,我能偶尔想起它,也只源于在人生的风景路上看到一处相似的景,恰似电视和电影里的序幕文字:“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轻巧的几个字符,道不尽的况味。梦里的我,站在土稻场上,向山脚下远望。模糊的坡影,绵延没有尽头,青青的麦苗在风里汇成一片绿色的波浪,悄无声息地起伏。有一条平展的小路嵌在麦地中间,那是爷爷奶奶和乡里人家来往的必经之路,是他们用脚步丈量修筑出来的。
路在绿色底板上蜿蜒,暮色苍苍,唯有路是白亮的,我看得很清楚。爷爷的身影没有出现在山路的尽头,去县城里参加村干部会的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等等吧,也许不要多时,在夕阳彻底从对面山崖顶掉落时,爷爷挑着包的身影会突然出现在“大石磙”(我们这帮小孩子对路口处一块大石头的起名,它有一人多高)的转弯处,他,回来啦!
我跳跃、欢呼,率先一溜烟地跑下稻场,从山坡道上向下飞奔。路陡,顺着山坡依势而修,呈“Z”字型,但我可不管能不能让疾跑的脚步及时在转弯处停住。我,仿佛腾云驾雾,风驰电掣,风在耳边呼啸,头顶的云被远远抛在身后。
近了,近了,我看见爷爷的白头发、花白胡茬,在橘红的夕色里,蒙上了一层昏黄的光晕,那时的我,哪里顾得去看他笑得合不拢的嘴巴和慈爱温厚的笑容。他的手是什么样?我记不得,只知道抢着帮他抱包,那里面可是装着好吃的。包,很重要,至于挑包的扁担,等姐姐和妹妹来拿吧。爷爷在道上走得不紧不慢,就像他在看庄稼,在和村里的人聊收成、聊家户人家的忧愁快乐。一袋旱烟里,笑也罢,感叹也罢,日子如奶奶菜园子里的韭菜,一茬茬割,又一茬茬长。“二娃子,跑慢点,莫摔倒。”爷爷在我的梦里喊着,声音沉入沟底山涧里。我回头张望,只见荒芜的黄土地上,“大石滚”旁的一棵歪脖子松树正孤零零的站着,天空是乌灰色,一只黑鸟“呜哇”一声从我头顶飞过。爷爷呢?他,不见了。他去哪里呢?我找不到。忽然,姐姐在坡上喊我,声音传得好远,她还是十一二岁的模样,脸红嘟嘟的,穿着花褂,袖着手站在核桃树下,喜鹊在树巢上探出半个身子,正衔着树枝在补巢。姐姐皱着眉头,难不成是不喜我抢了爷爷的包么?哼,我可不怕,奶奶最疼她,爷爷可是最疼我。爷爷许是找徐大伯唠嗑去了吧,甭管了。
我气喘嘘嘘地跑到核桃树下,白毛狗讨好地冲上前来,一个劲地冲我摇尾巴。“走,奶奶喊我们去菜园子摘菜,”姐姐没好气的扫我一眼。“行,等我一会,先放爷爷的包。”低下头,我看到手中,竟什么也没有,空空的,包呢?我疑惑。“赶紧走,免得奶奶拎不动”。姐姐催促道。踌躇的我,挪动脚步,只有跟着姐姐向前走。明明已是薄暮冥冥,为什么四处景色依然清晰入目?
我分明看见,黑瓦白墙的土房呈“┌”型安静地卧在平坦的道场上,厨房的屋檐下,安置着奶奶的鸡圈,鸡已回笼,或伏稻草窝或蹲在桁架上,间或能听见梦寐似的“咕咕”声。多年后,有一次在乡间宴请友人,饭前去屋外漫步闲游,也是夕阳欲颓、晚霞铺天的时候,我们看见鸡们竟也站在木杆上,迟迟不下,顿时想起《诗经》中“鸡栖于埘,日之夕矣”,更想起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奶奶的鸡喂得好,个个会下蛋,尤其是那只骄傲的芦花鸡。堂屋外的走道上,摆放着几盆花草,有指甲花、太阳花、千年矮、红豆杉苗,其中一盆种着葱绿的蒜苗。还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儿,修长的茎干,顶端开出浓缩版的荷花朵儿,花瓣的颜色渐变,由淡紫晕染为熏紫,花心是黄蕊。常常,有黑腹黄条纹的蜜蜂围着它飞飞停停,啜着蜜,闻着淡香,想来蜜蜂也是欢喜的。
“快走,还在看什么呀?”姐姐扭过身问道。“没看什么,就来!”我瞅了瞅稻场远处的柴场,一根根花栎树堆放在角落,柴棚子下面是码放整齐的一垛垛长短一致的木柴,沉郁辛厚的新鲜木材味道还在空气里弥漫。走下三级土台阶,到了幺爹的家院。几棵椿树笔直地挺立在道场下,叶子在晚风里发出“沙沙沙”的声响。蝉儿在浓密的树叶间,不停歇的嘶鸣,它们快活着,喧闹着。这么快就到夏季了吗?又是粘知了的时候啦!眼前的画面纷转:幺爹的三儿子拿着一张粘网(自制的,在长杆的顶端绑上一个铁丝圆圈,再套上一个网兜,固定),蹑手蹑脚地靠近最高大的一棵椿树,站在树下,侧着耳朵静听,认准声音的来处后,用粘网兜头一扣,只听一声尖锐高昂的“zi”响,接着就是在网内拼命扑腾时发出的“知了,知了,知了”的短促响亮的求救声。大家立即围上前去,争着在网兜里捞知了。抓住它玩什么?当然是先用一根长长的棉绳栓住蝉的一只大腿,捏紧绳端,然后放开它。这小东西,自以为瞬间可以逃脱,立即颤动翅膀,快如疾箭,冲天而窜。未想,冲至一半,就被绳牵缚,上下不得,只有“知了知了,知,知……”噪鸣不停。可惜,这样的乐趣短暂,总会被大人们及时喝止,因为,系知了所用的棉绳是偷拿的,那是要用来“zai”被套用的,不能瞎浪费。
我跟上姐姐的脚步,经过幺妈家的厨房,探头一望,黑漆一片,人呢?往常这时候,煤油灯应该点起来了,光线虽然不通明,但灶间的炉火红亮,映射在被熏黑的土墙上,光影重重,幺爹一家六口围着掉了漆的木桌在吃饭。幺妈总是给二爷夹菜,饭碗里堆满软烂的蹄膀肉、青豇豆、紫茄子。我还能听见红娃(幺爹大女儿)喝苞谷糁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声响,她一定是急着吃完要找我们去玩耍。有星光闪耀的明亮夜空,有皎洁月色入户的晚上,我们这两院内的六个孩子,可以有无穷无尽的乐趣:跳沙包、木头人、抓特务、抓子、藏猫儿……道场里的欢笑声,大人们纳凉时的聊天声,还有蛐蛐在翠绿的牛筋草里“札札”鸣叫,时而近,时而远,像水连天的暮云,如徐玉诺的诗句——小孩子醉眠在他的故乡里了。
竹林深处的小鸟被我和姐姐的脚步声惊扰,扑哧着翅膀飞起,长长的黑白色尾羽在林梢上划过,最终停留在梨树上,它转动着黑亮的圆眼睛,歪着头从高向下看着我们。我兴奋地说:“姐,我们把它逮住给三妹玩。”“想得美,你逮得住?这鸟最精。”姐姐笑我。树上的鸟儿也像听懂我们的对话,它一边卖弄着婉转的歌喉,一边在枝头欢快地跳上跃下,把才结出来的玻璃球大小的青梨摇晃的像个铃铛。奶奶种的这些梨树,每年结出的果又甜又香,摘下一个咬上一口,肉脆,汁多,送给幺爹和在阴坡上住着的徐大伯、宝哥们品尝,都说好。奶奶呢?菜园子里不见她的身影,松柏丛边的庄稼地里也没看见弯腰劳作的她。姐姐有些紧张,四处张望,大声喊着奶奶,没有人应。我看见,白雾升起,树、草、山林缥缈迷离,苞谷地有一条小路直通向前方。姐姐攥牢我的手,拉扯着我快速地向前奔跑,我喘息着,看不见脚下,只知道拼命地跑。跑呀,跑呀,跑呀,慌张与陌生的感觉如洪潮倾泻而至,我和姐姐陷入巨浪的漩涡中。爷爷,奶奶,你们在哪里呀?!前面突然出现两座坟茔,我惊慌失措的停下来,梦里的我害怕极了。空气似乎凝滞,白雾更甚,天空开始飘起雪花,唯有姐姐掌心中的温热给我带来了巨大安慰。“别过去,别过去,我们回家吧”,眼泪不由地淌下来,我对姐姐说。掉头就走的我们,一路奔跑,跌跌撞撞,耳畔风声呼呼作响,眼前树影丛丛倒退。我看见奶奶的菜园篱笆倒塌歪斜,园子里一片杂草肆意生长;松柏林旁的那口老井,泉眼干涸,井里的落叶已是厚厚一层;梨树开满如雪的花,花瓣纷扬落下,漫天都是惊心的白。爷爷的房屋在仓黄的天底下,萧索的立着,黑瓦白墙的鲜明不复存在,房梁裸露,土墙剥落,檐下只剩下几个残损破旧的空泥盆,那些明妍的花儿早已在光阴里凋败。“我知道爷爷奶奶去哪里了!”姐姐望向我,泪水打湿了衣襟。她凄楚地回望走过的路,在很远很远的路的尽头,有两座矮矮的坟茔,高高的墓碑将我们挡在外面……我的梦,醒了!霜白的月色落在相框上,照片中的人脸模糊又熟悉,“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漫长的冬夜里,谁的眼泪再也没有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