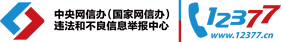老宅门前种有一棵枇杷树,是爷爷奶奶年轻时栽的苗。
从我记事起,每年盼着的,小满过后,总有枇杷。母亲手里的颗颗黄金丸,清香鲜甜,偶有几只果子留着鸟虫叮咬的残损痕迹,嘴角溢出的丰满汁水,挂牵着悠悠的夏天。
不曾上学时,枇杷树成了我和堂弟最亲的玩伴。顺着树枝延伸的方向,无需任何工具,双手合抱,两只脚配合着在适合落下的地方用力。那时候胆小又恐高,往往树没爬上去,衣服裤子倒挂烂了不少,免不了一顿责备,可这股顽劣的热情不曾熄灭。
父母工作繁忙,往往会推迟回老屋团聚的时间。我们攀上枇杷树,摇晃着脑袋,早早的便是期盼,甚至茶饭不思。爬的高了,视野越发开阔,近处,是大片连绵不断的农田,在天空下伸展,在大地上蔓延,冬日的微风扶着泥土散发的芳香,把出苗的冬麦驯化的精神抖擞。远处,薄薄的雾气在草地的空隙里慢慢地穿行,碎石子铺成的乡间小路蜿蜒着不见尽头,而身后是风吹日晒雨淋后的老宅,房顶的瓦片上布满了深色的青苔,房梁间悬着蛛网,柴房前堆积着淡黄色的木头,墙皮上那一层淡淡的石灰,是历史转过的年轮,偶尔回头会瞧见奶奶自顾的坐在角落里,顺着枇杷树的方向注视远方,路的那边有着老人家数不清的牵挂。
后来一场夜雨,打破了时光里所有的静谧,老宅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已经快要坍塌了,被洗刷后显得格外不堪和落魄。爸爸决定在老屋不远处买下了新房,是靠着马路边的洋楼,平坦的大路不再雨天泥泞,宽敞明亮的房间不再拥挤,周边甚至有让人欢喜的小超市。只是夜里飞驰而过的汽车交替闪烁着光芒,刺的人眼睛生疼,震天的鸣笛打破了以往的安静。那棵枇杷树,已经慢慢被遗忘了。
奶奶走后,我去祭拜,路过老宅。最先入眼的,是那棵已经在记忆里生灰的树,枝叶涛涛,蓬勃肆意。弯腰拾起滚落在地上小果,拂去灰尘,入口是酸涩,我皱着眉头才想起如今还未立夏,幼时黄澄澄、暖洋洋的小太阳也被忘却了模样。伫立良久,才发现和它亲近时,谈不上贵重,如今疏远了,倒是稀罕。老宅倒塌后,我们带走了一切,唯独留下了枇杷树。望着这棵繁茂的树,郁郁葱葱间有些星星点点的明黄,我突然替它少许难过,困于逼仄又弃于自由,离于闹市而忘于心扉,寂寞地扎根,守望着残砖碎瓦,一年又一年,兀自地热闹,却从未辜负过任何一个季节的雨水阳光,永远年轻苍翠,结着硕大的果子。有人来食便馈及味蕾,无人光顾便归赠大地,亦温情,亦爽朗。
老一辈种下它的时候,也许钟情于枇杷的寓意——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却不曾想过经历了大半载的风雨阳光,见证了三代人成长的枇杷树,如今依旧枝繁叶茂、绿荫如盖,悄然守护着我们,埋藏着不曾说出口的心愿。恍惚间,生命里留下的枇杷,已是深深款款,扎根在驷之过隙的岁月里,伸展出细细密密的想念。
如今老宅重修,水泥大道覆盖了陌上田间,枇杷树被留了下来,大抵是刻意不舍得挪动它。粗壮的主干是一脉相承的血液流淌,抽枝散叶间是恒久的深情迟迟不散,几经搬迁后又相互陪伴,多年之后,亭亭如盖的,又何止是枇杷?
当年读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时,末尾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流传千古,泪流满面,可惜年少不知意,再懂已是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