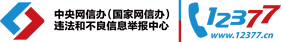老屋是用黄土堆砌的。
当我看到它的时候,确确实实只剩下了土堆。后来,土堆长出比人高的玉米,年复一年地茂盛成油绿油绿的墙,或是帐。
地上种了庄稼,地下又是什么呢?
从前,父亲很少讲关于老屋的事。但,他总对奶奶念叨:“老屋高头那块儿苞谷还没施肥”“老屋高头那块儿田挖了一半儿”……
我不止一次问“老屋是哪儿啊?”,他们总笑笑,解释两句我听不懂的话,就没有后续了。更可气的是,我问在那里长大的姐姐,她敷衍我的回答是:“就是老屋那儿啊!”
父亲给我们讲过他的童年。小学时,他把核桃带到学校卖,一颗颗核桃换成一支支笔,一个个本子。核桃树就长在老屋附近。我坚信能换学习用品的核桃,定然是比普通的核桃好吃百倍的。
核桃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铅笔也总是会用到握不住的时候。父亲会给笔头套上竹杆儿,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有时,还会捡同学扔掉的笔头。而竹杆儿则来自老屋前的老竹林。
一说起小学,他会满脸自豪地说:“那个时候我还当班长呢!”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小学时老师要求带跳绳,我看都不看商店里花花绿绿的跳绳一眼,把家里插秧时用的绳子剪下一截,就带学校去了。操场上,老师问“跳绳呢?”我摊开手,老师一脸惊愕。
去老屋的路上,要翻越数不清的大坎小坎。快到山顶时,停下,朝下看,山脚的红瓦房子变成一只只红蚂蚁。每棵树都高得看不到顶。树冠里,鸟雀们用层叠的树枝树叶儿隐藏自己,只用叽叽喳喳的鸟语,向同伴汇报有陌生人入境的消息。是的,在它们,包括树眼里,我当然是个陌生人。
我好奇地打量着一切,老屋呢?老屋是哪儿?眼前只有一块儿翻了一半的田。一块儿,是叶子枯老发脆的黄豆田。一块儿,是花残叶黄、土地干裂的藕田。
核桃树呢?
砍了。
奶奶一边回答,一边挥舞锄头,每一锄头都很用力,又很小心,挖得深而细,似乎在期待下一锄能挖出些什么宝贝来。
这一趟我还是没完全弄明白老屋的过去。但,起码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一一老屋是座房子。而我去的地方,可能只是地名叫老屋吧。
太阳从大雾里挣扎出来时,已近正午,大地散发出一片灿烂新鲜的金黄。父亲从田里回来,火急火燎地说,老竹林被推平了。等我们到了老竹林,很多人都在那儿,三五成群说着闲话,东走西看,像在逛市场。一些人单脚踩着捆成捆的竹子和他人说笑,一些竹子半截儿被土埋没,只露出一点儿凌厉的刀锋,仿佛在小心地掩饰罪行。周围高大的榆树掩饰不住伤心,频频摇动叶子——不忍心看这里变成了竹子的屠宰场。老屋场,早不属于我们,竹林自然也就失去了庇护。
空气中,竹子的清香格外浓烈,浓得叫人几乎落泪。奶奶掂一掂倒地的竹子,摸一摸伏地的枝叶,叹息一声接一声,但无人理会。秋风揉乱她的头发,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她叹息带走似的。
那天中午,父亲靠着椅子,讲起了他参军时的故事,讲他参军时的物件儿悉数带回。我想看,他沉默了会儿,说“都落在老屋没拿下来……”我顿时明白为什么奶奶翻老屋那块地总是很用力,因为泥土之下,藏着印“参军光荣”的陶瓷缸,带红花的军绿色大背包,军绿色搪瓷牙缸子……
黄昏,父亲去老屋翻地,我也跟去了。没有竹林陪伴的老屋彻底荒芜了,像一夜白头的将军。枯叶在空中打转,飘飞,落地。父亲一锄头翻过去,它就被埋进了土里。
原来,我所站之处,那个名为老屋的地方,在许多年前,是有鸡在院子、竹林漫步的。它偶尔低头,一啄,红鸡冠颤动,于是终结了一粒种子挣脱黑暗的梦;土房子周围还开满了蔷薇花、牵牛花,蝴蝶与蜜蜂结伴而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老屋的人儿一样的劳碌辛苦。炊烟每天按时升起,烟囱黢黑,连白亮亮的月光都洗不干净它。
现在,谁也不知道它们在地下又在继续怎样的故事。或许,它们的祥和与快乐早就停止在多年前那个推土机轰隆轰隆降临的阴霾冬日。
但我有直觉,郁郁葱葱的玉米是老屋长出的头发;核桃树和老竹林在地下继续生长;竹林里的鸡鸣声若隐若现;蝴蝶、蜜蜂在花丛间嬉闹;炊烟缓缓消散在晚风里。
也许,父亲当年的老物件儿正在土层深处沉睡,清风一吹,就闯进故人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