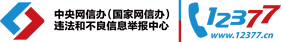出生在马桥中坪的孩子,小时候大多对“大渠”和“大曲”这俩名称傻傻分不清。总以为把大曲水装进坛子,再舀出来装进瓶子,放在待客的餐桌上,就是人们口口称赞的大“渠”酒。识字后,我在一次席面上,与酒瓶包装上的“马桥大曲酒”大眼瞪小眼,无比惊讶。仿佛多年熟络的玩伴,突然拿出他的身份证质问我:“你居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盯着酒,父亲盯着我,显得无比欣慰,他大概有些小得意:我这娃儿从小就对大曲酒这么感兴趣,难得啊。
于是,那年夏末父亲向我发出诚挚的邀请:娃,我去割水蒿你去不去啊?
我自然满口答应。一上路,我就后悔了。烈日悬在头顶,似乎有要把万物烤干烤透烤焦的架势。我看着晒得发红的两条胳膊,心里暗自叫苦。
山叠着山围成圆圈,麻雀结伴从这个山腰飞到那个山头,双腿机械地朝前迈,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数不清我到底问了多少句“还有多远”。一开始,父亲回答“再翻两个坡就到了”。后来,就简短的回“快了”。再后来,干脆不理我。口干舌燥的我再也问不出一个字,就和父亲一样,闷头向前走。
父亲时不时随手揪一片叶子放在嘴边吹响。没有旋律,那是父亲的童年,特有的曲调在山洼荡啊荡。树枝上挂着的鸟儿闻声而起。树摆摆手,与鸟儿作别。
蝉鸣愈发刺耳。太阳被吵得受不了了,躲到山后寻清静。流水声也渐渐明朗,一条溪流在山脚演奏了不知道多少年。
就这儿了。父亲说,靠着西岸边的大石头向四周看看,汗顺着额头流到衣领里,衣服像泼了水一样贴在身上。风一吹,是夏日才有的清凉与爽快。
割水蒿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儿,我干得极其敷衍。水蒿东倒一棵西歪几根,懒散地在野地野蛮地生长,东闯西撞,像个醉汉。小飞虫密压压地聚成一团,在一个地方飞很久。实在无聊,我扔下镰刀,悄悄在溪边捧一捧水,然后一扑小水滴,就精准地落在父亲身上了。“招呼一会儿有长虫来咬你!”父亲笑着吓唬我。我吃了一惊,乖乖地跟在他身边,不敢再瞎跑了。
码齐的水蒿好像一座小山,父亲抓住系好的绳子,扛起一座绿山。我们一前一后回家去,把晚风中变凉的夕阳甩在身后。
酒坊的院子里,水蒿堆得满满当当。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蒿味儿,青森森的,熏得人发晕。
蒸大曲酒,最重要的是制作酒曲。一块好酒曲,关键在踩。父亲把装好的酒曲放进特制的木框,然后就是一顿猛踩。他忙着脚下的活,也不忘和旁边的人唠家常。我看着踩曲这么简单,也急着要试试。可真正踩上去,才知处处皆学问。由于粮食在蒸煮后必须马上踩,避免冷却后干硬无法制曲,所以酒曲一般放凉一小会儿就要踩,踩上去既使再烫脚也不能停步,还得踩出四周实中间松的形状便于发酵。这可真不容易!
踩好的酒曲搬进密闭的屋子,水蒿就派上用场了。在地面铺一层水蒿放一层酒曲,之间留一定缝隙填充水蒿,然后一层一层像砌墙一样码满整个屋子。
然后,就是等待。
落叶起舞的季节,时不时飘着酒香提醒人们:该蒸酒了。酒曲终于重见天日,很快又被送进酒坊,经过大火的洗礼,酒曲在渡最后一劫后涅槃重生,终于酒香四溢,喷薄欲出,似要踏平酒坊。
最终,酒曲一分为二各得其所。精华被储存进酒坛,标上“马桥大曲”。另一半被冠以酒糟之名,晒干作饲料(吃它长大的猪,肉质细嫩)。刚出炉的酒糟热气升腾,酒香相当一部分由它们散发出。
酒坊主人好客,留蒸酒的人一起吃晚饭。开了坛,陈了十年的大曲酒被倒进酒壶,围着炭火,发出滋滋的声响。酒香与空气混合,酒没入喉,人就似乎醉了,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
饭桌上,人们互相敬酒说着吉利的话客套的话打趣的话,欢声笑语充斥着整个餐厅。有的人醉了,上半身伏在饭桌上,旁边坐的人还想拉他起来继续喝,可怎么也拉不动,原来他自己也醉得手脚发软了。
我和父亲走在回家的路上,说着以前,“你小时候,嗯,还是个小奶娃儿的时候,就喝过酒呢,就是拿筷子蘸一滴喂……”“对,我记得那时候,三爷最喜欢这样逗我。”“那时候筷子尖儿的一滴大曲酒,辣得你脸红扑扑的,没一会儿就摇头晃脑拍着手连说好喝好喝…”
马桥大曲酒当真厉害。全靠岁月把酒香封存沉淀着,几年后,酒坛开封时,香飘云外,几乎要掀翻房顶的架势。
去年寒假,再次与那熟悉的香味儿相遇。酒糟铺在路边晒着,风打那儿路过,糠尘飘扬,细小的尘粒飘呀,飘呀,把酒香弥散在冬日温暖的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