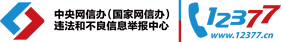油与酒同属水形,异曲同工的取自稼穑,本来疑似孪生兄弟,但性相近习相远,它们南辕北辙分道扬镳,一个气宇轩昂地登堂入席奔了个锦绣前程,尽享着人世间的风流快活;一个逆来顺受地俯首下厨拣了个瓦罐蜗居,备受了锅底里的烟火煎熬。翻阅历史文化记载,总有英雄豪杰把酒当歌、文人骚客纵酒放歌,咏叹着把“酒”字泼洒得诗词歌赋里满眼皆是。天下的宴席,有美酒必有佳肴,有佳肴必有油盐,油用醇厚的养分把贪吃好喝的大家伙儿喂养得脑满肠肥、肚腩凸起,可一旦离席哪个不割袍断义的忘个干净利落,纵使油嗝连连油屁悠悠,谁曾为这个擦亮锅底铺垫生活的“油”字留下片言只语?
那年,队里腾出库房开办“育红班”,收拢半大不小的孩子牙牙学语启蒙教育。“育红班”名字响亮,但吹糠见米近乎现在的学前班,不过孩子年龄跨度较大,从五六岁到八九岁不等,像一陇茬口不齐的韭菜。油坊与教室近在咫尺,一溜儿摆开四间房屋。尽管它外表强大但体质极度虚弱,厚重的板门十有八九挂着一把锈锁。孩童顽劣好奇,几天就把油坊窗户的薄膜抠挖出千疮百孔,洞悉了其中的秘密。里面,除一间独立开门外,其余三间联相互通,靠四根立柱举重似的托起两排山架;东边倚墙垒筑着一方倾斜的灶台,锅口里高外低不成体统,黑黝黝的威风凛凛,有随时扑过来生吞活物的样子;南墙窗户边是硕大的碾台,端坐着一米过径的石轱辘,给人一种被碾过喊疼的沉重感;北墙那边直愣愣地躺着一件不知名的家伙,暗泛着乌黑的油光,还空中吊、地上立着配套着好多设施,像战斗电影里鬼子们经常使用的刑具,惹得孩童们一片争议和猜测。后来年岁稍大的孩子释疑解惑:躺着的是榨筒,吊着的是榨杆,圆的铁环是饼箍,方的木块是撞楔;如此云云,不一而足。末了还画蛇添足,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榨油的场景,舔唇咂舌地夸张着曾经缥缈的油香。孔子曰“食、色性也”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成为社会性的困惑时,草根百姓面向自然深度挖掘,铺垫生活的油料也广泛取材灵活运用,棉籽油、漆油、木梓油、核桃油、羊油等等,尽管它们都有“油”的名字,尽管它们有的麻口、有的涩嘴,有的让人结肚、有的令人腹泻,但它们毕竟能够一滴、两滴地为锅底碗口渲染一点油气,为劳累的日子奉上一声叹息,为艰辛的生活抹开一丝亮色。这群清汤寡水里拖过来的孩娃,都有狗的嗅觉和猫的馋劲儿,撒泡尿照照,哪个没有嗅见别家油荤蹭着不走却被父母扯着耳朵牵回来的丑闻。如今面对真实的榨油家什,孩子们就蠢蠢欲动得张开想象的翅膀,时刻巴望着碾盘吱吱得转起来,榨杆嗵嗵得撞起来,油汁咝咝得流出来。流啊流啊,流得传阅翻看的小人书上口水斑驳,流得老师不时训斥,流得同学一片窃笑。
时光的步伐踏进了寒冬,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又下了一场,把天下粉饰得太平。冬末腊初,油坊的大门终于开了,下了课的孩子们就鸟雀儿一样扑棱棱地飞向油坊。腿脚还没有过去,久违的香气却丝丝缕缕地扯进鼻孔,把野马般的顽童振奋得扬鬃奋蹄,衔枚疾进。油坊内,靠墙斜立的锅台上正在翻炒菜籽,一人向灶膛里不停地添柴旺火,火苗的舌头偶尔窜出灶门东倒西歪地晃来晃去,小孩忙不迭地围上去分享温暖;看另一人双手抵着月牙状的木掀顺着锅底将菜籽由低向高推去,氤氲中虫卵样圆滑的菜籽从高处流下来又被推上去,好多回合后满锅的乌黑渐成茶黄,就转身拿藤质的器具盛了摊晾在碾盘上。屁孩儿心比天高想去推转石碾博个喝彩,哪知三五个凑成团憋得脸红也只把碾框撼得吱吱呀呀作响,大人在一旁笑道:回你妈怀里吃几年奶,再来!孩子们脸皮薄一哄而散。课间又悄悄的蜇了过来,却见人牵健壮的牯牛拉着碾子一圈一圈、一圈接着一圈地转,碾子吱吱呀呀像是喊着口令,把人的两只脚、牛的四条腿喊得十分合拍,大家屏声静气不敢惊扰。抬眼寻觅,另一处也生起了灶火,按照工艺流程可能要蒸煮碾成粉末的菜籽了。午间时分,油坊里氤氲弥漫,热气蒸腾向上融化着屋顶的积雪,油坊檐下的点点滴滴无法成线,菜籽浓郁的芳香却借风生势不断蔓延和扩散,向因雪停工猫在家中的乡亲们发出了真挚的邀请。哎,踏雪寻香文雅事,父老乡亲却扯淡,他们开门出屋大步流星,把古典诗词的美妙意境踏在脚下踩得一片泥泞。对他们而言,平平仄仄的唐诗三百首,只有李绅《悯农》的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能够提气安神,无论筋骨劳伤还是身心疲惫,它都像一贴膏药直抵病灶给人疗效,给人深深的安慰。
跨进油坊的大门,甩掉即将陪伴一冬的破袄,乡亲们麻利地挽起袖子加入装饼入箍的阵营。随着队伍的壮大,师傅又指挥着一拨人将油饼一块块地置入榨筒内再用木楔挤紧。要开榨了,后生犊子早已候在榨杆两旁,一个师傅在榨尾拉着绳子以保证足够的力度,另一个师傅在榨头掌握方向好保持准头,见榨头师傅带着大家后退、仰身,榨尾师傅就亮开嗓子,声音洪亮悠长:都攒劲哟——,榨头师傅大吼一声“嘿哟,撞——”大家步调一致向前冲去,带有铁箍榨头与木楔相撞,发出惊天动地的“咣当”声,宛如电影片段教堂里祈福的钟声。一声声号子,一次次加木楔;一次次加木楔,又一声声号子……如此这般重复后,榨油的汉子们脚步更紧了,步履也变得沉重而迟缓,喊出的号子也越来越短促。当撞榨的汉子们脱去身上最后一件衣褂时,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脊背上纷纷滚落下来,醇香的菜油就从油榨下丝丝缕缕、绵延不绝地流向油槽。间或有人替补,就歇下来伸展指头揩油去滋润枯燥许久的嘴唇,也算是给清水肠胃递上一声问候,献上一份薄礼。今天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Ⅱ季)《心传》浮光掠影地再现了榨油的工艺流程,时尚的视觉盛宴与没落的传统技术对接,惹得国人好生叹息和哀婉。今天的人们在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同时,深深怀念那些渐行渐远的传统工艺,这种追忆过去的情愫可以理解,但往事不堪回首,真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那年那月的那些磨难,谁愿意回到从前!
第二天上学,孩子们又多了揩油的内容。小家伙一副清水肠子,平日里油腥稍重肚肠就咕咕噜噜的唱反调,而今不知轻重反复揩油,上午还飞毛腿似的下午却瘟疫般腹泻的腿脚发飘,茅房里先是此起彼伏后来便铺摆得下不了脚。老师通知队里的赤脚医生,扯了几把草药熬成黄冽冽的汤水喝下几次,才陆续缓解局面。当然,榨油的号子仅维持几天也戛然而止,农作物的一再减产让偌大的油坊昙花一现后迅速沉寂下来。年底,队里分配油料的标准论两计算,我家五口人分得3.9斤菜油、11斤饼渣。识字不多的母亲像解析几何难题一样,千方百计添加辅助线条,开源节流破解困境,让微不足道的油汁浸润着生活如缕不绝,步步挺进。
直到第二年秋季我们转入另一所学校,油坊始终紧锁着,再后来也只是偶尔象征性地敞开一丝儿缝隙,从自弃走向自灭,空留一片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它的吝啬、冷漠和无情激励着我们发奋图强,鞭策着农家子弟及早深入生活,从在家煮饭、喂猪到野外放牛、割草,再到上山砍柴、挖药,大家茁壮成长步步向上,把童年的影子烙印在故乡的山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