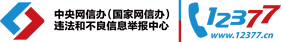老家毗邻享有盛名的神农架,背枕青山怀抱秀水。那山不知何处而来,偏与神农架茫茫山脉缠绵纠结的难分难解,群峰蜿蜒层峦叠嶂地奔向云海,也不知何处去了。只有那水知根知底的源自神农架,几曲几折地婉转流来,把二十多公里的路程走了千年万年,至今不歇脚步。水一路穿插让人感到好生辛苦,慈爱的家乡铺设着开阔的河床,让它伸展腰身自由流淌。道法自然,水也充满感激,它血液一样滋育着这一方土地,并且羞涩的透露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粉水。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粉水》:“取此水以渍粉,则皓耀鲜洁,有异众流。”由此可见,家乡漏制粉条的历史源远流长并且可能在一定的历史区间享有盛名。但千百年的蹉跎岁月中,朝代更替、社会变革、战事烽火、瘟疫灾害,一切物事皆可能朝兴夕废,湮灭在历史的册页中,给人们留下美学的思考和叹息。等我们走出懵懂开启童智时,往事已越千年,漏制粉条更是黯然褪色,宛如光与影的碎片残留在乡村生活的某个角落,仅在红薯、洋芋意外多收了三五斗时才被想起。红薯、洋芋是庄稼人的亲密伙伴,更是当时生活舞台上耀眼的明星,能客串主食、菜肴,还能游走在人畜之间,有今天影视歌三栖星秀的味道。但物多必贱,堆放久了容易长芽、生斑,沦为生活的垃圾。善于探索的人民启迪智慧,把它们改造成既能长期储存又方便入口的样子,也有进一步贴近生活的意思。但它起于何时何代谁是开山鼻祖,无法寻根溯源剖析究竟,连学识渊博的百度百科也说得模糊:粉条是以豆类、薯类和杂粮为原料加工制成的丝状或条状干燥淀粉制品;在我国有千余年的历史,各地均有生产,呈灰白色、黄色或黄褐色,为干制品。
与酒坊和油坊比较,粉坊的待遇极不公平。它躲在仓库晒场外边一个低洼的角落里,不伦不类的两间房屋显得卑微,还有些破败。用现代流行语言来说,就是被边缘化了。那时我们少不更事,缺乏起码的知识储量去把它从寂寞中唤醒,然后展开一次深刻的对话,挖掘家乡粉条盛衰起落的历史传承,再挤上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专车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傻得天真笨得可爱,把家乡的粉条、粉丝吃了一碗又一碗,吃了一年又一年,哪个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瞒过舌尖穿过喉咙一步到胃,谁曾吹开过碗口的葱花去寻找碗底的文化?世事往往就这样扑朔迷离,等你觉悟时,历史不仅断层而且裂为碎片,天女散花般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怎么找也找不回来了。
粉坊的门锁经风历雨锈得牢固,滴入柴油浸了才极不情愿松脱。推开门,灰尘天网罩下来抖得满头满脸,几个人嘴里吐着“呸、呸”腿脚却跨了进去。夏来人人忙,农事件件急。田间地头庄稼需要精心侍弄,今年土豆丰收,近来日头毒辣,更是漏粉好天气。庄稼人敦厚实诚,又怀着从野外劳动转入室内作业避免日头炙烤的感激,胳膊腿儿格外轻快利落,三下五除二就让粉坊告别了脏乱差。接下来洗净洋芋蛋蛋剁碎,一勺一勺喂入石磨推成糊糊倒进滤布里挤出白乎乎的浆水,待沉淀后缓缓篦去上面的水,再取出沉积物暴晒干透后就是淀粉了。文化的说法,就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起初没有机械设备,这事做起来耗时费力,石磨分头作业咿咿呀呀推得大家腰上添酸腿上添软,后来镇上有了加工厂,粉碎机汹涌而下,一袋烟的功夫就完事,为古老的传统工艺送上现代文明的曙光,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南宋诗人陆游写下《苦热》的日子就是漏粉的好日子。社会化大生产的年代,大家一呼百应,很容易组成繁忙、壮观的劳动场面。丢下早饭的碗筷,掌瓢师傅大步流星地奔向粉坊时,几十号人物已经到位。大海航行靠舵手,漏粉全凭瓢师傅,今天的船他是舵手,乡人直肠子,三言两语就将任务到人。一时间,挑水的、生火的、摆器具的、搬淀粉的、置案板的,不一而足,忙出热闹的气象。拉开阵势后,第一道工序是搅和淀粉。在农村男人很少上锅台,但漏粉的面必得大老爷们搅和才行,这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稠了,粉条不匀、漏起来太涩;稀了,粉条成不了形、容易断脱,还要一边漏一边和不能歇气,只有灵巧而剽悍的男人才行。第二道工序是漏粉。掌瓢师傅赤膊上阵,手臂伸长端着粉瓢沿着锅口画圈儿,让稀稠相宜的淀粉糊糊从瓢眼里漏下来,连绵不绝地滑落在滚烫的开水锅里。这活儿技术含量高,可也苦字当头,癞汉子望而生畏。不说那葫芦瓢份量沉重,三四个壮汉团团围住一瓢紧接一瓢的加粉,不能留空儿;难的是半蹲在锅台上,上身挺直,眼睛要盯着锅里,单手举瓢另一只手握拳不停地锤打,而且端瓢的手还要不停地来回游走,以免锅里的粉条粘在一起。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而下面锅水滚开热浪翻腾,把棉布裤衩也濡得透湿,着实抵不住就喝住“添瓢”的汉子,跳下来大口喘气。偏有人拿他婆娘开涮,“还不去看看那卵蛋蒸熟没有,怕今晚有双黄蛋吃了!”骂声和哄笑声中,拨锅的、起面的却不敢懈怠,忙活着把粉条从锅里捞起来,横过木杖担了小跑着丢进门外的腰盆,砸起一团耀眼的水花。
大人忙,孩子们更忙。那过年杀猪才用的腰盆如今一溜儿摆开,浴盆似的都盛满清水,太阳当空一照明亮亮的晃眼。这道工序是“洗粉”,把起锅的粉条置入清水中,捞洗后担在木棍上捋顺,最后上架“晒粉”。洗粉时难免残断或遗留些粉头,孩娃们就蝌蚪样的撅着一排屁股趴在盆沿上,个个伸长小手在水中争夺。有人念日子清苦存仁爱之心,捞洗时故意留下一绺半缕的,就近的孩子抓住这头往嘴里送去赶紧吸溜,旁边小手的伸手去扯那头,一时虎口拔牙多的犹如哪吒来了一般,片刻间扯的细碎。有猴性的娃们,你争我夺时起了真火,开打后双方赤膊加上汗水滑不溜秋的,只能泥鳅样在地上你翻我滚,吃了亏的就抱住对方腿脚不放陷入僵局。间隙,里面传来“让开,粉来了--”,两人瞬间脱手复活,又奔在一个盆里捞干搅稀。也有狗性的崽子,动了怒气不言不语却在背后下手,冷不丁地兜住别人屁股,一个倒栽葱地掀翻在水盆里,把水花扑腾的到处都是。一盆水,七八担呢,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挑来容易吗?就有大人从扫把中抽出竹条作势要打,把孩子撵得鸟兽散,但家鸡撵得团团转,檐水依然滴旧窝,不消片刻又悄悄潜了回来,照旧在乡亲们的眼皮底下嬉戏、乐呵,把童年的岁月演绎成乡情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