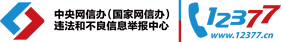我蛰伏已久的思想时常被一种朴素的声响击醒,这声响不是黄钟大吕的大雅之音,也不是阳春白雪的丝竹弹奏,而是一种来自乡村的、很有节奏的“扑、啪”,“扑、啪”的乡村弹唱。奏出这种朴素弹唱的是一种在荆山乡村随处可见的简单农具——连枷,弹奏的人正是我那经年月久耕作在黄土地上的父母亲。
连枷,由一根长竹竿作柄,通过一根短小简洁的木柚,将一组土楠木木条编织而成的木条排连接而成。翻开连枷的前世,据说还曾是士兵守城御敌的兵器。然而,在我认识它时,它早已弃戎从农,“复员”回到了广阔农村的稻场之上,成为乡村的一种古老的脱粒农具。
“连枷响,麦登场”。记忆中,每年五月,成捆的麦子被收回家后,父亲就选一个晴好的天气,将麦捆打散,均匀铺晒在扫干净的稻场上。待晒上个把小时以后,便与忙完家务的母亲一南一北相对而立打起连枷来。
就像唱歌要有人起头一样,打连枷要一个人先打。一般是母亲先打,她轻轻舞起连枷,连枷在空中轮了一个圆,然后“扑”地一声落在麦穗上,紧跟着父亲便在母亲连枷起落之处,“啪”地补上一下。母亲的体力稍弱,连枷落下去的声音是较为轻柔“扑”,而父亲却孔武有力,落下去的声音是那种掷地有声、很有穿透力的“啪”。他们二人默契配合,一起一落,一轻一重,缓急有序,整场推进,“扑”“啪”之声连贯而有节奏,相呼相应,奏响老家上空经久的丰收民谣!随着连枷的轮番敲打,熟透晒枯的麦穗纷纷脱离麦草,散落在稻场之上。一场麦子打完后,母亲就忙着去和猪食喂猪,父亲就用另外一种简单的农具——一个大树杈削制而成的东西,我们称作为“羊杈”,将那些麦穗翻个身,再晾晒一段时间后,继续拍打。麦草打烂以后,麦粒也基本干净了,这些麦草便被堆了起来。如此循环,一天下来,要打上两三场。
在老家,连枷其实是被称作“连盖”的,当我后来知道“连枷”二字的写法之后,再联想起打连枷时的场景,发现将“连枷”称呼为“连盖”,还是最为形象的。
需要用连枷来脱粒的,除了小麦,还有秋天的黄豆、小豆等豆类作物。打黄豆和小豆的劳动量不是十分大,所以多数是我们跟母亲一起完成的。
和许多事情一样,打连枷也是一件看着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在母亲手中轻巧如飞、灵动自如的连枷不知道为何一到我们手中,就显得那么不听话、不配合。于是母亲便一边示范一边给我们讲解技巧,然而凭我们的理解和实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很快领悟的。我们只得打一下,然后让它的柄在手中特意翻个身,再笨拙地拍打。打着打着,不知道怎么搞的,弟弟竟然先我一步,玩转了连枷。我的面子上便有些挂不住,更加心浮气躁地舞起来,然而越是急躁越玩不转。于是索性顺其自然地,用老办法继续拍打,打着打着,却不知道怎么地一下,也玩会了,自然也少不了一阵自我表扬式的雀跃欢呼!
学会了打连枷以后,我们便学着父母的样子,相对而立,你一下,我一下,像模像样地打起场来。起初,还是有节奏地弹奏,打着打着,便有了戏耍的成份,“噼噼啪啪”杂乱无章的响声,就像一群牛踏上了木板桥。有时一不小心,连枷前面的木排就拍到了对方的脚上、头上,然后便是推推搡搡,最后,力量弱的人便哭喊起来。最后收场子的往往是母亲,她一面将我们各人都教训了一顿,一面将我们剩下的那些半拉子活完成。
在年复一年的连枷声中,我们一天天长大,最后离开了生我们养我们的村庄,劳动的细节离我们越来越远,慢慢地淡出我的记忆,而连枷这种古老的农具和农事却依旧活跃在我思维的村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