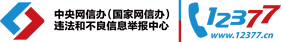父亲是一本书。对于儿女来说,父亲是我们的必读书。世上书万卷,其他的书都可以不读,但父亲这本书非读不可。如果不读父亲,我们就不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更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读父亲这本书,我们必须要明确重点。只有把重点弄明确了,我们才能找到读父亲的正确方向。否则,我们就会把父亲读偏,读错,甚至读反。在父亲这本书中,重点无疑是父亲对我们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恩和教育之恩。因此,我们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来读父亲。读父亲对我们的呵护,读父亲对我们的疼爱,读父亲对我们的付出。只有抓住了这个重点,读父亲才有意义。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背我爬山上五虎的情景。父亲当年三十出头,被马良供销社派往五虎分销店当会计。我那时五岁左右,跟着母亲在老家油菜坡生活。有一次,父亲回家看望我们,要走的时候,我突然抱住了他的腿,哭着闹着要去五虎玩。父亲稍微犹豫了一下,便答应了我。当时五虎不通车,一路上全靠步行。从油菜坡到重阳那段路还算平坦,我都是自己走的,且走得欢天喜地。可一过重阳,上五虎的那条山路,突然就像梯子一样竖起来了。在那陡峭的山路上,我只勉强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两条腿又酸又疼,一点儿劲也没有。这时,父亲双膝一弯蹲在了我面前,扭过脖子对我说,趴我背上吧。我一听高兴坏了,马上趴在了父亲的背上,还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头。那条山路有十几里长,从山脚爬到山顶少说也要两个钟头。父亲刚背上我的时候还不太吃力,但走了一段就开始喘气了。我听见他喘气的声音越来越粗,越来越快,有点儿像耕田的牛。往前再走一段,父亲身上就出汗了,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额头和鼻尖直往下滚,背上的衣裳也打湿了,头发里冒着热气,好像上了气的蒸笼。我那会儿少不更事,还不懂得心疼人,见父亲累成那样,也不知道下地走几步。爬到半山腰,父亲实在累得吃不住,便把我放下来歇了一会儿。他这时嘴里渴得厉害,就去路边石缝里找水喝。但当时天旱,石缝里的泉水都干了。父亲没找到水,却发现了一树红果子。他折来一枝红果子对我说,我给你吃红果子,吃了自己再走一段儿吧。那枝红果子红得像火,吃在嘴里酸甜酸甜的,味道好极了。吃过红果子,我就自己走起来。可是,我只走了几步就停下了。山路太陡,我的脚抬都抬不动。父亲见我不走了,只好又在我面前蹲下,让我再次趴到他背上。父亲背我爬山的时候,生怕我从他背上掉下来,一直都把两只手反过来搂着我的屁股。汗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都顾不得擦。后来眼睛看不清路了,父亲才对我说,华娃子,你把我眼皮上的汗擦一下吧。天色黄昏时,父亲终于把我背上了五虎山巅。这时,父亲已经累瘫了。他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好半天都站不起来。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送我的确良黄裤子的情景。当时我在保康一中读书,吃住都在学校。父亲那会儿在店垭工作,每个月都要找机会进城一趟,给我送生活费和粮票。那年春夏之交,一款叫的确良的黄裤子突然在城里流行起来。的确良是一种化工新布,布纹细密,颜色纯正,形态飘逸,做成裤子穿在身上又美观又舒服。我们的老师差不多都穿上了的确良黄裤子,同学中也有穿的,当然都是城里的干部子弟。看着别人穿着这么时髦的黄裤子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心里当然也羡慕,但不敢奢望。因为我们家兄弟多,父亲的工资又不高,吃穿上只能将就。不过,当时天气已经热起来,我身上穿的还是一条过冬的灰布厚裤,心想要是能有一条薄点儿的裤子就好了。一天傍晚,父亲又来学校给我送生活费和粮票,居然也穿着一条的确良黄裤子。一看见父亲的黄裤子,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直了。父亲注意到了我的神情,随即低头看了看我的灰布厚裤,还伸过手来在我的裤子上摸了一下。有些热吧?父亲摸着我的裤子问。我愣了愣说,还好。这次,父亲把生活费和粮票给我后,没像以往那样马上和我分手。他让我跟他去了他住的那个旅社。进到旅社房间后,父亲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一只旅行包,从中掏出了一条半新的蓝布裤子。我以为父亲要把这条蓝布裤子送给我,心里不由暗自欢喜。但是,父亲没有把蓝布裤子给我,而是换下了他身上的那条的确良黄裤子。我正感到纳闷儿,父亲把他刚脱下来的的确良黄裤子朝我递了过来。这条裤子给你穿!父亲说。我顿时愣呆了,迟迟不敢接那条黄裤子。父亲催我说,拿着呀!天热了,你那条灰裤子也穿不住了!直到这时,我才确信父亲真是要把他的的确良黄裤子送给我。接过黄裤子,父亲要我立刻把身上的灰布厚裤换下来。我把的确良黄裤子穿上的时候,心里差点乐开了花。看着我笑得嘴都合不拢,父亲也笑了。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送我上大学时给我扛箱子的情景。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考上了位于省城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父亲那时患有严重痣疮,一旦发作便难受得要命。不巧的是,我正要上学的时候,父亲的痣疮突然发了,可他还是坚持要把我送到襄阳上火车。从保康到襄阳那天,我们坐的是一辆货车。父亲与那位司机很熟,搭他的顺风车,除了想省点钱,主要还是我带了一个又重又大的木箱,坐班车很不方便。车过南漳境内的黄花岭时,父亲要司机停了一次车。他说要去上个厕所。父亲上厕所用了很长时间,回到车上时脸色苍白。司机问他,怎么啦?父亲皱着眉头说,痣疮发了,屙了好多血。那天到达襄阳,已是下午五点多钟。司机要急着去卸货,一到襄城就把我们父子丢下了,连同那个又重又大的木箱。火车站在樊城,还隔着一条汉江。父亲本来说坐公交车去火车站的,可那个木箱太大,公交车上不了,因此我们父子俩只好步行。我那是第一次到襄阳,不清楚从襄城到樊城有多远。父亲扛着箱子走在前面,我背着一个包跟在他屁股后头。那个木箱实在是又重又大,父亲必须头肩并用才能把它扛住。木箱把父亲的头沉沉地压在下面,他一边勾着头走路,还要一边仰起眼睛辩认方向,显得十分别扭而艰难。加上父亲的痣疮又发了,所以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迈得非常吃力。走到到襄江商场门口,我提出换父亲扛一会儿箱子,可他没同意。父亲说,你扛不动的!他说完继续往前走,步子忽然加快了一些。大约走了两个钟头,我们总算到了火车站。父亲把箱子放下来的时候,他的脖子全都磨红了,而脸色却更加苍白,看上去像一张白纸。
每当想到以上这些让我终生难忘的细节,我对父亲的感恩之心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当然,父亲也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也曾经令我伤心过,比如在一个放寒假的雪天,我碰到了一辆运货的卡车,便从黄坪坐到了父亲当时工作的店垭,想去他那儿玩上一天。我到的时候,父亲正在和同事打扑克。见到我,父亲显得很冷淡,也没问我是否吃过午饭,只顾着继续玩牌。那辆卡车卸完货,父亲当即就让我坐那车返回了。父亲也曾骂过我,比如有一次在桌上吃饭,我的嘴巴吃得太响,父亲忽然瞪我一眼说,你嘴巴轻点儿好不好?巴达巴达的,难道你是猪啊!父亲还让我吃过皮肉之苦,比如有一回家里的半包烟不翼而飞,父亲怀疑是我和老二顺强其中一个拿走了,可一时又不能确定是谁,于是他就找来一根竹棍,命令我和顺强轮流互打。我打顺强时很轻,而顺强打我时却下手很重,像母亲平时用棒头捶衣裳。其实拿走那半包烟的是老三顺勇,许久之后他才自己承认。
然而,我绝对不会因为父亲曾经冷落过我、咒骂过我、痛打过我而记恨他。与父亲对我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恩和教育之恩比起来,这些细枝末节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们读父亲这本书,千万不能避重就轻,舍本求末,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只顾着一味地去责怪父亲的粗心、鲁莽和凶狠,而把父亲对我们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再说,父亲也是个凡人,他也有自己的兴趣,也有自己的个性,也有自己的脾气,偶尔的疏忽,偶尔的暴躁,偶尔的失误,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作为儿女,如果我们对父亲一时的过错念念不忘,并且耿耿于怀,甚至当作不敬不孝的借口,那我们就未免太狭隘了,太偏激了,太荒唐了。倘若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当儿女的,不是缺心眼就是缺良心。
不过,父亲是一本大书。面对父亲这本大书,暂时读不懂也不要紧。在我看来,读父亲是一辈子的事,只要我们用时间来读,用阅历来读,用情感来读,用全身心来读,总有一天会把父亲读懂的。